八月的葬歌
一六年八月一日建军节,外公躺在医院,被隔离,家属戴口罩探望。那天下午他已经不咳了,但一直喘着。医生说出院吧,没用了。
外公在医院呆了整整两个月。七月中旬,我从学校回去第一次看他,已经瘦了很多,孱弱的坐在病床边缘,眼睛盯着前方,满是迷茫和虚空。他用瘦骨嶙峋的双手颤抖着捧起水杯,哆哆嗦嗦喝一口,喝了又吐出来。双脚肿胀,始终放在垃圾桶的桶沿上。没法下地,走几步就喘。嘴里吐唾沫,病床近手边就是一卷白色的卫生纸,吐了擦,擦了吐。他的手一直哆嗦着,扯了一把又一把的纸。垃圾桶里也全是纸,白花花的,分外煞眼睛。
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没想到外公已经病得这么重了。刚进病房,他对着我说,放假啦?我说,是。没过十几分钟,他又转过头来,你放假啦?我说,是的,是啊,我放假啦!医院待的太久和各种药物的副作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神志不清了。
可八月一号的那天下午,他突然清醒了,前所未有的清醒。大人们都知道,外公的时日不多了,于是整个家族不顾一切往老家赶。落叶归根,这是外公的心愿。决定了,便即刻启程。前前后后共三辆车,外公在最前面的救护车里,我在最后一辆。这车出发最晚,追着外公的车一路疾驰。
可我知道,我和外公的距离怎么也追不上了,那是遥远的生和死的距离。人生一世,生老病死,千里奔丧,大抵如此了。
车队全部到达已经夜里十点。简单安置后,所有的家人都围着外公坐着,都想着能看几眼就看几眼。等大人们出去吃饭了,我一个人挨着外公坐着。我就看着他,他的胸口一起一伏,喘气很困难,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头困乏的老水牛。他的手一直摸索着外衣的口袋,试图拿什么东西。他想拉开拉链,拉了两次才拉开。摸索半天,拿出一把钱,用卫生纸心相印的包装纸装着。他艰难的扯出右边那沓,而后拿给我,让我数数。我小心翼翼的数了一遍,"有七百","九百啊?"。我说,"七百呢!","哦"。说完他睁大眼睛思考着。接着他又把另一沓十块二十块的给了我,我又数了数,一共一百三五元。半晌,外公没再说话。
后来,外公叫来了舅舅,姨妈和最小的女儿,我的妈妈。外公给了妈妈两百,又给了姨妈两百,还有外婆,剩下的零碎全给了舅舅和舅妈。他在分家产了,他说:“没有多少,你们都拿着发财。”外公神智又清醒了,知道自己大限以至。我转过头,悄悄擦掉了眼泪。
第二天八点三十六分,我还在喊着“外公,外公……”,可我知道永远喊不应了。外公走了。他是我第二个看着走的老人,也许是第二次亲历死亡,我多了些淡定,可是泪还是留不住。
我慢慢懂得所谓死亡,是去世时亲人的两行清泪和嚎啕大哭,是再也没有源头的思念和无奈,是天人两隔的遥远,也是不可能再回头的时间。
陶潜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为期三天的葬礼结束,外公于清晨化为坟冢归去了。我有些害怕,正如陶潜所说,活着的人不会因为逝去的人而停止生活,也许有一天就忘记了。远方的人说,时间会治愈的,慢慢就好了。可我说,时间在治愈的同时也会遗忘,有些人是不是随着时间渐渐远去了。他没回答我,我想啊,答案是肯定的。
外公走的时候,我们忙着悲伤,过了好久才想起外婆。其实比起外公,外婆更可怜。以后她就是一个人了,面对偌大的房,漫长的夜,孤枕难眠,刻骨铭心。
回想起来,那天外婆一个人躺在黑黢黢的小房间里,左手拿着卫生纸抵着眼角,我知道她在淌泪,我也知道了什么叫老泪纵横。“他算是满足啦!要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外婆一边擦泪一边说着,“他总以为自己是老大,我算是服侍了他一辈子。这两个月,在医院也是服侍够了。他后来记性不好了,自己吃了东西偏说是我吃的,大半夜的骂我,那我受不了了就去走廊站着……”,外婆都在说外公不好,可是她怎么会一直流泪呢?外婆舍不得外公所以才一直说他不好吧。这么多年,无论风雨都过来了,从此便孤身一人,我想她可能苍老得更快了。
想起那天,葬礼现场的烟火一阵又一阵,巨大的烟幕升起,又渐渐散去。而关于外公,他正一个人孤零零的躺着,在棺材里。外面是连绵不断的葬歌以及道士先生敲锣打鼓,嘴里念着我们听不懂的经文。
葬礼三天,每天都有磅礴大雨,漫山遍野的都是悲伤。大雨带走了外公的身体,把他灵魂丢给了夏天。
天地时辰,时起时沉,返程无期。
那个夏天,有暖烘烘的太阳,还有冰冷的啤酒。可是啊,这样的夏天我一点都不喜欢。
扫描二维码加关注,获取更多精彩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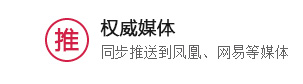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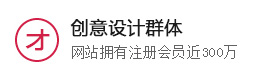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