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暴中的合唱
寒风把窗帘上的洞吹的更多更大了,窗户玩忽职守,这块灰白的布在冬日的早晨剧烈颤抖。“唔……”窗帘下的棉被里探出一个乱蓬蓬的脑袋,茫然的看了看,好像来到了一个新的星球。
“唉,今年刚入冬就这么大的风……得把挡板安上了。”这个十平米的矮小棚屋被这一张板床塞得满满当当,为了留住窗边暖气的温度,就只能牺牲窗子的好处。冬天单是风就这么讨厌,他还是最喜欢夏天,那时破旧的窗帘也能映出些许绿色,些许生命的律动,阳光透过树叶间隙,再透过窗帘上的缝隙,一片破碎的光影倾洒,给这拥挤的屋里添几分生气。窗户的上端墙面开裂的有些厉害,他便把挂槽竖着挂在床边,再把有挂钩的一端系上一根绳子,下摆钉在窗子另一边,造出了一个竖着升拉的窗帘,百页窗一般。等微风来邀窗帘共舞,屋里也上演一场光与影的舞蹈,又好似一曲无声的歌唱。
无奈,自然把韶华给了盛夏,他自己的音乐会也只属于盛夏,眼下到了寒冬,他也只得用木板挡严这位夏天的演奏家。
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三年了。
繁闹的城中是叫卖声的殿堂,此起彼伏着呼告、传扬与竞争,四处可见的广告牌上24小时播出着各类广告,穿梭不息的车流携带这天的清晨却单调的出奇,每个大小不一的显示屏上,每个瞳孔中的屏幕里,都紧急插播这一条消息:太阳活动异常。
拖着疲惫的身躯出门,穿戴好护具制服,凌晨五点开始送外卖,直到晚上11点再回到这个住处。白天的太阳和风雨、车流和红绿灯、晚点的焦急和责怪还有同行眼疾手快的抢单,似一双双悬挂在天上的眼睛注视着他的灵魂,似一把把辫子抽打着他的脊背,然而更令他浑若走钢丝的,是他不愿放弃的一个追求——做一个自由的画家。
然而今天却实在反常,打开手机后没有一份订单,各个应用的界面只有一条单调的消息——中国气象台红色警报:太阳活动异常,请勿外出。
这句话着实有些惊人,一改往日委婉的“建议”“尽量”之说,却改成了一种命令般的语气。还在疑惑之中,却突然发现,手机突然没有了信号,面部拂过一丝麻麻的感觉。恐慌也如这麻麻的感觉一般短暂,他想,如果是太阳风暴影响了通讯,去公园里坐坐也好,就当是这中年大叔为自己放了一天假。
前一晚,太阳活动突然增强了好几个量级,广袤的金色光球上黑子与耀斑闪烁不停,日珥一个接一个升起,好似暴雨时的池塘,水花却只是溅起却不会下跌。然而“早上”跟“晚上”的概念不适用于星际间,世界各国都在揣测,究竟是太阳的寿命估计有误,还是身边某种中扰动引起的这一切,更有阴谋论者揣测是哪个超级大国的秘密武器实验……新闻混杂各种分析的误导在各类媒体上刚刚显露头角,就被一份份红头文件抹去,各国纷纷进入战斗预警,边境双方剑拔弩张,平时的停车场全部肃清作为防空洞,近地的无线电通讯几乎完全断绝,而空间卫星几乎全部报废,各国通过光缆才实现通讯,纷纷表明自己是这场事故的受害者,而非肇事者。
然而各国都是受害者的话,肇事者就只能是那个炽热的巨大天体了。
……一个个变电厂报废停工,电网逐渐陷入瘫痪,人们的恐慌就像一堆干燥的木柴,等待一颗将其点燃的火星。于是,这颗火星来了,从极地蔓延至赤道的巨大“彩虹”不断地变幻着形状,如被扼住咽喉的人慌乱挣扎的手臂。地球的磁场在剧烈颤动,几乎被太阳的盛怒屏蔽的频谱里掩盖着地球的啜泣。
走出门后,太阳似乎格外耀眼,风却仍然又干又冷,看到的是如同以往,五点钟空荡荡的大街。脸上的麻痒感再次袭来,越发强烈。到了公园的松树下,他拿出手机想要诵几句诗,却发现这方寸屏幕黑色中有一缕灰烟的形状——哑了。“这次的太阳活动好强啊,还是说那整天被人们诅咒臭氧层终于坚持不住了。”他心想,“去看看她吧,她订不了餐,说不定现在正对着面包片一副苦大仇怨呢。”
这株松树在公园的一角,早上老人们来这儿练太极,深夜时情侣相聚于此看着夜空把心事倾泻。他是在这里第一次遇到的她,看着阳光难透过密密麻麻的松针,只在边缘上留下分叉不平的荫影.他来为她送餐,电话里的声音很甜,语调很客气,请他把东西送到公园一角的松树下,她穿着一身简朴的蓝棉衫。松树下只有她一人,靠坐着树干,两眼看着地面上的树荫,两抹柔顺的柳叶眉黛微蹙,沉思着什么。沉思的女子是大自然的雕塑,天使般的气质令人不敢久视又不愿移目,松下的她宛若水中莲花,远观而不可亵玩。他不愿打破这平静的美丽,手中餐盒的香味却如此不和谐,美食竟也令人生厌。她缓缓抬起头,正正看着他的双眼。
“我的外卖吗?”
“…哦哦对,是…您吧,在松树下的蓝衣姑娘。”他怔怔地与她对视,赶忙把目光甩到地上。话已出口,才觉好像现在称呼姑娘都不用“姑娘”一词了。瞳孔又不住的上浮,一抹清茶般的微笑飘入眼帘。“不好意思啊,里,啊不,您在这儿做什么啊?”“哦?看这松树的影子边缘很像我研究的课题里的那个星云,就在想工作上的事儿,我藏的这么靠里不好找的吧?麻烦您了。”“哦哦,没事,看来您是搞学术的,真厉害呢……那我就,我就走了。”“嗯,谢谢了。”“没事没事儿。”踏上电动车,他匆忙地继续去送下一单,脸上的焦急却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难掩的笑意。
自那之后,他每天中午都会留意,有没有来自那公园附近的订单。他把那个地址和电话记得倒背如流,又抢到几次,为她送餐,慢慢地了解了她的事情。心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躁动与恐慌,他知道那是一个幻想,像走钢丝一样,心和手在万丈深渊上彷徨。
她的住处就在这公园的一旁,四楼的高度既能看得更远又不会感到身悬天宇隔绝人气,阳台一侧就是这松树冠,从上向下能看到树底看不到的粒粒松果。她是附近大学天体物理的研究生,近来一直在研究小行星带,希望能够通过探索其起源以及构成来判断小行星带会对火星造成什么影响,为这位地球的孪生兄弟保驾护航。毕竟,有一天我们或许要去那里生活。
在耀眼的太阳光里,他走到了那棵松树旁,松针倒也是霸道,阳光再强也没能穿透这层层阻隔。“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他反身望去,她正在阳台上向他招手“你怎么还出来了,今天政府下了命令,禁止一切非必要外出,你在这里晃悠是会被抓起……你是?”“哦哦,我不知道啊,手机坏了,街上的广告牌也报废了,什么消息也看不到。”眉头微蹙,她暗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凄然一笑“没办法,只是徒劳。”又打量了一下这个在怪异的清晨来到这里的怪异的人“你是那个外卖小哥儿吧!”她的眼中又溢出了光彩,绷紧的双手松开栏杆“先来我们这儿避一避吧,不然今天的辐射过去你可能会得癌症的,还可能会有人在街上巡逻把你抓起来。”“呃,这……”“没事,不用拘谨,反正没多少时间了。”
“没多少时间了?”眉头微蹙,他也紧张起来,声音微颤“这是……什么意——”话没说完
防空警报刺穿了空气。
“……34,35,36,三十六秒的预警报,难道这样的太阳活动下还有国家能发动空袭?”“不会的,现代军用飞机的操纵、导航、瞄准以及各类武器几乎都是自动化的,而这种量级的太阳活动几乎让所有的电子设备报废了,变电厂也逃不了,还有……”“那就好,大不了再回到‘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嘛。”凄然的笑有映在她的脸庞“如果能的话,倒是万幸了…如果只是生活用电中断的确不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如果核电站也‘停电’了呢?”
“……那备用电源”“不会了,这次的灾难影响的不是电能输送,而是所有的电气元件——我们只是失去了对电,对一切高效率能源的控制,然而那些聚变反应堆却没有死去。还记得那年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泄漏吗?那就是停电后的反应堆热量无法导出导致的灾难。”“看来我们终究是个作茧自缚的种群,不过应该还能保证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吧。”“就算真的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时间的问题,更何况,早就有一批牺牲者了——他们住在那儿”她伸出食指向上指了指。
4小时前,太阳的亮度骤然增加,紧随而上的是第一次日冕疯狂生成与破裂,水星的微弱的磁场几乎被扯碎,岩浆从灰色的岩石层下迸出,流淌;接着是金星的大气发出了超长的极光,一条条绿色的亮线在漆黑的空间里跃动如同乱坟岗里的鬼火……这一切都被天宫站里的5名航天员观测到,然而他们也大体知道,这就是大自然送给他们最后的晚餐——一次视觉盛宴。太阳的粒子风暴是不可见的滔天巨浪,转眼间就将脆弱的空间站吞噬,尽管外表面上没有一丝划痕,可这能耐受大气压强的铁皮终究耐受不了质子风暴的轰击。防护舱门还没来得及开启,已经有大量的仪器失灵,仪表乱转。“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来自来自三个国家的兄弟姐妹紧紧相拥,漂浮着旋转,球形的泪珠起起伏伏,《国际歌》的音符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舱外是无边的宇宙翻滚着无声而汹涌的粒子巨浪,舱内是渺小的地球之子飘荡着声泪俱下的相拥合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Debout !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Debout ! les forcats de la faim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ère :C’est l’éruption dela fin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Du passé faisons table rase Foule esclave,debout !debout !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Nous ne sommes rien,soyons tout !
水星、金星的惨象是从天宫发出的最后一条消息,也就是这个时候各国发现空间卫星几乎全部失灵。联合国还没有探清局势之时,各国政府却不约而同地拉响了防空警报,引导公民进入防空洞避难,可谓是近代以来最为一致协调的国际行动。然而直至疏散几乎完成,还是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能够找出这次太阳灾难的肇因,直至太阳第一次慢慢平息。
就是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了弦乐家。
2.消失的星空
偌大的太平洋横亘在地球的背阳面,一艘远航的邮轮离开檀香山前往东京。船长在舱中正闭目养神,看他的神情似乎随时都能从椅子上跳起与暴风雨搏斗,眼睑上深深的皱纹如石雕一般坚定,浓密的眉毛和刚硬的络腮胡铜须一般。驾驶舱来电,通讯受到干扰,他缓缓睁开了双眼,看着漆黑无比的天空,月亮和星星全然没了影踪,于是捻灭了手中的香烟,又揣上一个嚼烟,带上帽子走出了舱门。“How in the world?”他指着天空,眼睛在海风中睁不开似的“二十分钟零五秒前我们刚刚欣赏了太平洋上壮观的落日,那时可是万里无云,现在上边儿这倒扣的碗底上连一个星子都没有?”“船长,我们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和外界通讯一直没有应答。”“那我们可就是失联了,趁着还早抓紧回港。”“船长,现在的导航全都失灵了,连罗盘都不能用,好像是地磁场出了什么状况,不然通讯怎么也同时中断……我们可能暂时被困在这里了”“……这应该是太阳风暴,二十年,我在海上漂了二十年,还从没见过这么蹊跷的事,可这天……通讯和导航干扰很可能是太阳风暴的影响,可这天为什么连一点儿光都——哦天哪,看北边儿!”一条绿色的光臂在远处延伸、挥舞“这是……”“极光,在赤道上的极光,看来,看不到星星倒不足为奇了。”说罢他掏出那块嚼烟“别紧张了,我们经守得住风浪,但对这样的力量没有办法,我们要被写进童话书里了。”
其实,他们是最先与弦乐者接触的人,蔓延到赤道的极光固然罕见,却并没有超出人类科学的理解范围,这突然黯淡,以致漆黑无光的夜空才是真正可怕的多——万里无云的天空上没有了星光和月亮。
海王星外的科伯依带上正展开一张巨大的网,那是一个沿着奥尔特星云内侧延展开来的一个等离子球壳,在一光年多的内径上生长,所到之处的星空全然被屏蔽,如同把太阳系包裹进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将系外的所有电磁波反射、吸收,从外侧看如同一粒黑色的珍珠不时地迸出一颗颗雨花石。这是弦乐家到来的脚步声,为了演奏,如同我们的演奏会不能允许市场的喧嚣叫喊,它也需要一个安静些的音乐厅,更要保护自己的琴。
等离子球壳的布置需要一定时间,弦乐家想要在演奏前要为自己选中的琴调音,于是它向那颗炽热的橘黄星球掷出了一颗致密的岩粒,紧接着便看到了光球上浮起的那一层层涟漪——一个个能装下三四个地球的日冕缓缓升起,那就是电磁场的弦。
弦乐家非常享受这深厚的音调,在等离子球壳搭建完毕后的效果更好。这个星系有一个天然的共振腔,紧挨着恒星的有四个致密的固态行星,而后是一圈厚度刚好的小行星带可以回环咏唱,再稍远处的气态行星还可打出节奏。
弦乐家是拨动弦的乐手,那片闪耀的星空中有着许多它曾经的演奏。而今它的又一个乐章,需要我们的太阳。
调音结束后,地球上的恐慌才真正爆发。
公园里的阳光又变得柔和,松树被照耀着,熠熠生辉。躲藏在草丛中的麻雀,埋身在鸟窝的喜鹊都探出头来,叽叽喳喳,不惧初冬的寒冷飞到枯枝上上歌唱,方才的光影梦一般虚幻,大地上的生机不减。鸟鸣声划破死一般的寂静,这是他和她在警报声后听到的第一种声音。“你听,应该没事儿了,”他爽朗地笑了,“应该没事儿了,咱……”“趁现在抓紧去防空洞!快!”她转过脸,忧愁更深了几分,“动物虽然比人的感官更灵敏,能感受到人感觉不到的异象,但它们不会深入思考,只能依靠本能。没有弄清这次太阳风暴的原因,谁也不能确定那个巨无霸什么时候会再发一次脾气……”“这次我们没有防备,但下回,难道依靠现在的技术还不能预测吗?”“这次的活动毫无规律,一反常态地打破了11年左右的周期,”她顿了顿,“我有一种感觉,但很荒诞,又有根据,我……”“那是什么?”“恒星光变。”
防空洞内,她遇到了几位自己的同事。“你来得这么晚,还好没事”一位带着厚厚的眼镜,穿着的文弱男子迎上前来,“这位是…”“啊,这是…我的朋友,咱们组里的人都在吗?我有个想法…”“是关于这次太阳活动的?”“嗯,但也只是猜想,只能勉强解释这次的现象,却找不出原因…”眼睛背后一个苍老而浑厚的声音响起:“你觉得是恒星光变还是太阳要步入老年?”那是一位头发花白却依然浓密的教授,身穿一身灰色的老式西服,戴着一副挂绳眼镜,眼神柔和坚定,双手缓缓扶着手杖从一个凳子上站起“导师,您也这么觉得?”“毕竟前些年塔比星光变的时候这个话题曾被炒得很热,我也闲来无事,看到过相关的模型,跟今天这发疯的太阳倒是很和脾气。好在现在的通讯恢复了一些,应急电力也多少有了供应,可以跟其他地方的人交流下意见了。”“可,好端端的太阳正值壮年,不会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迸动起来啊…”这时,他有些恐慌地向这位博学的老者说道,“恒星光变就是这样的异常太阳风吗?”“哦,当然不是这样单纯,好比太阳原是一个稳定的灯泡,数十年间亮度也不会波动超过1%,但它突然变成了一颗跳动的心脏,那样庞大的质量会膨胀收缩,不过向外迸出的血液是辐射、粒子,是难以想象的能量。”片刻的沉默后,他问道“我们能挺过去吗?”“不能。”老者干脆利落地答道。
“完全是无稽之谈,就算你的猜想能够解释一些现象,但也终究是猜想,根本没有实际证据,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联合国支持的天文学家研讨大会上,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究在对这个大胆提出的猜想进行着反驳,却少有人能提出些没有政治意图的猜想“但眼下的所有现象都能很好的用脉动变光星的模型解释,而我们需要这样的答案”“这不是我们需要的答案,这根本就不是答案,我们要的是因果律,是根据律,不是小孩子觉得什么像别的什么就有了智者的感觉。”“而且,这个模型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异象”,“太阳风暴侵袭之时,天宫站上的宇航员发挥的最后一条讯息显示,太阳表面突然产生了剧烈的日冕爆发,与此同时,地球背阳面的星空消失了。”“星空消失?”
“进一步探测,应该是等离子体屏蔽技术,只不过覆盖范围简直难以想象——就像沿着奥尔特星云生出了一层罩子,几乎将系外的电磁波段全部屏蔽。”“……这两者一定关联,而且即使太阳活动异常可能是自然现象,等离子屏障绝对不可能是自发形成的。”“We’ve Got Company!”“而且,既然能影响到太阳,他们离我们可能已经相当近了。”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从早到晚的讨论会,试图从太阳风暴与等离子体屏障进行关联,来推出这些潜伏者们的目的。她在导师那里帮不上忙,有太多伛偻着身躯的白发老头在从各种花里胡哨的理论去解释太阳光变,还有些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在前苏联的档案中翻找等离子体隐身技术的资料,想要尽快击溃这硕大无比的星系艮壁,击破这个真正“不透光”的牢笼……
她没有了以往课题研究时的神采,家中的电视里嘈杂的新闻,把各地掀起暴乱的不安再散洋到世界各地,地球的自传仍在继续,夜半球的人们在有月亮的夜晚或许察觉不到不对劲,因为他们早已不再仰望群星;可等到无月的夜晚各地的人们终于发现,有人偷走了他们的星星。没有了星光的璀璨,没有了闪目的车灯霓虹,从防空洞的入口望去,从各式各样的掩体中望去,惨淡的夜空如同吸人的无底深渊,偶尔出现的新月如同死神的镰刀。当各国的政府再次用电缆发送通报,说明等离子体屏障一事,并未提到对“他们”的猜测,然而恐慌是民众们“智慧”的启蒙者,通报一出就有各地的防护措施内发生躁动,反社会者联合对自己受难的同胞烧杀奸淫,末日恐怖主义的浪潮掀起;还有宗教徒们突然抖擞了精神,高举着《圣经》宣扬末日的审判已经来到……中国的防护设施相对比较安全,然而这个在欧亚大陆的东隅繁衍了5000多年的文明知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倘若太阳再次产生一次一次大规模的光变,很可能会提前退出主序星,进而膨胀到地球的轨道,与其在这末日的边缘堕落,他们宁愿选择守住为人的尊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3.他和她
当知晓了天宫站上的一切后,她终于难以为继,在防空洞的角落里靠墙坐着,双臂环抱着双腿,受委屈的孩子一般,那双装得下星辰大海,飘飞着星际尘埃的慧眼,如今装不下两行凄楚无奈的泪滴。他背着手走到她身边,缓缓蹲下“你知道吗,”他向她探去“我好像知道‘他们’的目的了,啧,也不能说是目的吧,但我觉得最近的两个异象是为了什么,我好像猜得到。”她忙伏在在裤子上藏好自己的泪,而后强装出一抹微笑来“哦?你怎么想呢?”“……”他看她那还红呼呼的眼眶,愣了愣神,想要说的“你怎么了”终于被锁在了喉咙里“我……我是这么想的,等离子体屏障是为了滤掉其他星系的电磁波,而太阳的光变是要放出太阳独特的电磁波,也就是说,这两者都是为了让独属太阳的电磁波在太阳系里增强,回荡。”“嗯,的确可以这样看,可‘他们’为什么要太阳的电磁波呢?而且太阳风暴还会放出大量的高能粒子,他们难道就不怕下手太重,太阳自己从内部击溃等离子体屏障吗?”“这些我不太明白,毕竟那些物理知识,你们才是行家,但这让我想起自己之前的一些事。我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可家里不富裕,后来上了大学,业余时间还是不愿放下这个爱好,但用来画画的材料很贵,笔、颜料、画架都还好,差不多的就能用很长时间,可纸就不一样了,如果画一次就用掉一整张纸甚至好几张纸,我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哈哈哈,想不到你还是一个才子啊”她的笑声里鼻音很重,但充满了阳光。“只是想罢了……于是我就把一整张纸分成四份,用细条吸墨纸把一张画纸分开,每个区域都可以画”“你是说,太阳的辐射是‘他们’画?可这画的价格也太昂贵了,有多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刚刚容貌焕发的她又沉郁了下去“你知道吗,天宫站上的宇航员里,有一位是我的父亲。”
她
南半球的星空要比北半球的靓丽许多。那年的八月,她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父亲坐在微风拂过的草地上,远处是蓝色薰衣草的海洋,星垂遍野,草带上了灰色,薰衣草染上了银色,闪烁的光吹起一阵阵夹杂着草香花香和泥土芬芳的浪,“倏倏”声宛如原野上夜的乐章。那是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想要看星星,可雾霾遍布的都市中只有反复回旋的霓虹,于是在他进行宇航员特训之前,带着她到新西兰的山坡上去看星星。她对父亲的这份礼物爱不释手,甚至想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描摹它的模样,她迷上了天体物理,因为星际间不只是只有单调的虚空和物质的交替,还有她的梦,还有人的梦,还有人的想象。
4.第三个异象
就在他们两个谈话时,第三个异象出现了。
一天天过去,太阳好像又恢复了宁静,然而人们对这次异象原因抑或“他们”的目的仍旧一无所知。在地球上的人们抢修电力设施,将重要设施装备转入地下的同时,连天文学家都有些惧怕的望远镜又传来了新的数据——水星轨道内出现了一个正在“生长”的圆环状结构。
每隔一定距离就会出现一个节点一样的装置,这个有着四千多万公里内径的圆环,每一个节点都有如一整个青藏高原,人们诧异其巨大,对其生长之快而觉无比惊讶,从出现的一个节点到圆环的首尾相连只用了四十六分钟零五秒,地球上接收到的光谱表明近300千米就会出现一个节点。天外来客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民众的恐慌只在于“他们”是上帝还是魔鬼,而学究们担忧的却是:“他们”有没有发现,在颗蓝色星球上有一个文明。
“圆环”上寂静后不久,地球上太阳的光谱再次突变,只是这次并非太阳的巨变,却是更加难以令人置信的——太阳的枷锁。那些节点突然展开、联结形成一个个巨大的吸盘样的屏障,给太阳扎上了一条黑色的腰带。“天呐……”地球上的一位观测者手中的图样颤抖着“这是,‘戴森环’?”
“嗨——嗨——知道吗?恢复部分电力后,有些卫星又运转起来……”他看到了在防空洞入口出神的她,依旧抱着双腿蹲在一角,便一路跑了过去。“但是,没有人看到天宫号。”她转过头,幽幽的眼神“啊……你已经知道了……”他也半蹲下来,“但也很可能是他们逃回了大气啊,而后降落在海上,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太空中连天宫号的一点痕迹都没有。你的父亲可能还活着。”“谢谢,”她的脸上又闪过那忧愁的微笑“我明白,我都明白……我不该这样消沉下去的。”她闭上眼,低下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吐出来,而后睁开了那双装得下星辰的眼睛“即使父亲不在那个狭小的空间中了,他依然存在着,在别人心里活着,就是在这宇宙间不灭。”她转过身来,玉臂终于放开了蜷缩着的双腿,向前俯去,双手轻轻扶住他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两片月季花瓣给叶子留下一道春的印记“真的谢谢你……”还没等他回神,她已经站起身离去。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位梦想家怎样揣测‘他们’的来意吧。”研讨会上,她的导师因之前的谈话还有他自己的态度而有些受针对“我还是坚决反对攻击。首先,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敌人,甚至可能还是朋友;另外,退一步讲,即是‘他们’不怀好意,敌我双方的技术差异是巨大的,一旦交火——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与我们交‘火’——我们根本毫无胜算,地球根本没有任何太空武器,一旦我们走错这一步,很可能会自挖坟墓。”“您说得不无道理,教授,可‘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太阳动手了,我们就在这里坐以待毙?我们不是羊!倘若‘他们’真的有恶意,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死。你们中国有句话‘等死,死国可乎?’我们即使灭亡也要有尊严的自己选择灭亡!”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发言表明了立场,简朴的会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老教授用手托住下巴一声不发,眼神被吸在地上。
散会后,她和他一起找到教授,询问近来有无进展。教授莞尔一笑道“还不明白吗?人类如今还是一个喜欢自己较劲的小孩。口口称称宣扬着的新时代,人们关注的还是农耕社会、原始社会时的东西,吃喝住行性,花样再变也还是同一个东西,而今真正有了外人,就害怕咯。不给人一个更伟大的目标、理想,人怎么可能变得更伟大,怎么可能会有‘新时代’呢?”
“教授,他们想要干什么?”“你觉得,当一个自私的孩子,一个很小,很幼稚的自私的孩子,发现自己的玩具被别的孩子拿着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噗……他会……又哭又闹……”她不禁笑出了声。“我们那儿对这些熊孩子有一句俗语叫‘一哭二闹三上吊’难道?”“我说过了,人类现在还是个孩子,哭是没有人听的,‘上吊’是最终的威胁,所以……”“人类要对‘他们’发动攻击?”“……嗯,虽然他们连要打哪里都不知道。那个‘戴森环’吗?只怕我们猴子一样的手臂够不到哪里。”
西太平洋安德森空军基地上的行动早在太阳刚刚恢复平静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各国都想用自己曾隐藏的技术在这个方寸小岛上堆砌出一座巴别塔。对“他们”的打击手段而今看来唯一可行的只有一种——太空子弹。对于水星轨道内侧的打击,数千万公里的行程中,距离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要在复杂的星际环境中保证武器打击尽可能少的发生偏离,否则只会给太阳送去一颗人造的小行星。对于这种超常规射程武器的控制只有两种途径:人工智能,或是量子通信。然而这两项技术都不成熟,何况‘他们’还很有可能做出某些回应,或说,反击。终于,在‘戴森环’出现以后,这个岛屿上也不再掩饰动作,三架掩藏在地下的火箭系统揭开了盖顶,锋锐的弹头直指苍穹。曾经风靡一时的量子通信如今却帮不上忙,尽管可靠,但通讯还是要借助电磁波,在这样的距离上光也要长途跋涉,高级AI却能自主的脱离地球上的操控自行接近那巨大的“戴森环”。
然而,考虑到工质推进器的局限,为了保留武器进入太空后有充足的动力推进,并且尽快的抵达目标而不被太阳的引力拉去失去控制,AI系统只能保留最基本的调整功能——人类的这把长矛几乎只有一个矛尖。更加不容乐观的是,在环绕太阳这个巨大“氢弹”的巨大装置面前,人类的所有的核武器攻击也如同杯水车薪,而威力更大的反物质武器仍然只是一个概念——人们现在只能在实验室中制备几个可怜的反物质粒子。于是,千万种设计之中,只有纯粹的动能武器能够有勉强的威力,人类向地外文明的第一次反击,竟是向他们掷去一颗石块。只不过挥出这颗石块的手是一颗超高当量氢弹,利用热核爆炸的能量促使推进液急剧气化而后将“石块”掷出。这颗凝聚了人类千万年的智慧的石块,就是真正的“后羿之弓”。
“戴森环”的出现平息了太阳风的威胁,防空设施中的人类在不怕被再次吹熄的显示屏上看到了全世界的军工合力建造的三枚“石块”——军方给他们的名字是“射日弓”“毕竟尖锐一些的东西会让人觉得更有威力,”她苦笑道“毕竟对于能够把我们所在太阳系的力量,我们能够接触到都是奇迹了。”“可这三发大导弹会不会激怒‘他们’啊?”“我倒觉得,‘他们’连什么是‘怒’都与你我,与整个人类全然不同——甚至根本没有我们所谓的情感与意志。老实说,我都快要皈依上帝了,当然,不是长的像人的上帝。”
三发射日的箭矢并没有被一起射出,人们决定保留一发以备万一。于是,在太阳星变的一个月后,从那颗渺小的蓝色星球上飞出了两粒微尘,向着太阳的项链上飘去。人们看到的却是气势恢宏的推进器点燃了大半个天空,被电离成等离子体的空气抟成发着亮光的巨柱,轰鸣着拱向天际。如果一切顺利,还要近一个月后人们才能够得知两粒“石头”的结局如何。然而,就在刚刚引力弹弓弹出月球轨道时,这两发“射日弓”却好似被一把无形的手逐层的拆解了开来,丑陋的铆钉螺母飞散在无边无际的虚空,推进器、计算机、氢弹维持舱、原子弹引燃舱等几个主要装置硕大无比,又有管线相连,好似被扯出的脏器。“戴森环”的转速突然变慢,从一个展开的节点上脱离下一个镜面一般光洁的柱体,在侧面上荒诞的静置着一个对称白色物体,与柱体相比蔓延出许多生硬的枝枝叉叉——那是完好的天宫号。
突然,天宫号沉入了柱体,而柱体却没有任何的变形或者伸缩。紧接着,柱体以惊人的速度移动着,在眨眼间从近乎太阳的表面来到了地球上的关岛,缓缓漂浮在海边,甚至没有惊动一片云彩,没有带动一丝风浪,静静地悬在沙地上,反射着周遭的每一滴水,每一寸天空,甚至是每一声鸟鸣,梦幻一样。
人们当然不会探测到这位来客,只是恐慌于两粒石头的遭遇。各大天文台的望远镜都聚焦在了被肢解的残骸,企图看清究竟是什么将人类最快最强的子弹弹指间打回原形,得到的却只有失望和更大的震惊——可观测到的每一份零件都是完整的,在近地轨道时尚未脱落的通讯器还在正常工作,并显示系统正常,这正是‘他们’的庖丁解牛。
与此同时,中国航空航天局的通讯段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波形,一个苍厚有力的声音传来:“停止行动,我们来解释一切。”
弦乐家
她的眼睛里喜悦和慌张交织在一起,渗出的一行清泪还挂在脸颊上。那个声音曾今是最为亲近的,又一度是最为遥远的,而今又回来了。从那瞬间移动的白色柱体中,天宫号被轻轻地放在沙滩上,舱门徐徐打开,她的父亲与曾经与他环抱,在太空中地球的注视下齐唱《国际歌》的兄弟姐妹们陆续走了出来。站在熟悉的土地上,他们凝望着蓝天,而后放任自己向后倒去,躺在地面上慢慢品尝阔别已久的新鲜空气。没有在此沉溺,他站起身,向自己的同胞发出了讯息。
隔离,消毒,各项检验,从太阳风暴中消失,又从太阳的镣铐上归来,天宫号的宇航员身上有太多的疑问与奇迹,返回地球后的第一条消息的语气颇像神明——当真正脱离母星时,人确是会发生一种蜕变。“‘他们’没有与我们进行语言上的交流,语言在当下的星际交流中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她的父亲在联合国的听证会上说道“但‘他们’还是成功与我们进行了交流,我们难以理解他们的语言——或说他们的语言已经退出了他们的历史——但她们却能明白我们的一切。”“在那场风暴里,你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啊,那场风暴!感觉就像昨天的事一样!我会向你们说明的,不要着急。不如我们换个称呼吧,‘他们’是‘弦乐家’,而那场突然的风暴不过是他们的的‘试音’”“您的意思是?”“老大的意思是,他们是一群音乐家,星际间的音乐家。”“不错,不过与我们的音乐大不相同。众所周知,我们的音乐,不论是钢琴还是古琴,不论是簧管还是竹笛,即使是口哨,归根到底也不过是各式各样的机械波,而机械波都只能在实体物质,固液气等摸得到看得着的物质中才能传播,而这也就限制了我们的音乐只能在大气层之内回荡——我们的音乐只是一种自言自语。”“您的意思是,‘弦乐家’的音乐是电磁波?”“不完全是,他们是真正的‘弦乐家’,不只是电磁波,就如同我们用机械波构成音乐,用电磁波看到画面、传递信息,‘弦乐家’用电磁波来谱曲。他们能够深入到更高的维度上,真正的梳理着‘弦’!他们能感受得到每一处时空的涟漪,每一个电子的跃迁,也能感受到每一次新星的爆发,每一次黑洞的喷流……他们放弃了在这深邃宽广到可怕的宇宙里用蜗牛一般的光速传递信息,他们其实只是‘他’一个,弦乐家只是一个。”“……你们是如何知道这些的?”“……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在风暴之中发生了什么。”
《国际歌》在空间站中回响之时,舷窗上突然没有了刺眼的光,没有了那颗蓝色的星球,他们的一切设备都恢复了正常,只是所有的信号都被拦截。而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团诡异的云团,各处不时地发出各种颜色的闪光——他们来到了奥尔特星云内侧的的等离子体球壳边际。宇航员们却并不知情,在这里太阳也变得和其他的星星无甚差异,他们甚至来不及恐慌,只想知道这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而产生的幻觉,然而看到同伴同样迷惑的神情,心中便回荡着一个声音:“这是哪里?怎么活下去?”
这时,他们第一次邂逅了那个白色柱体。
不由分说地,柱体突然展成一个平面,播放着太阳系各个星体的画面,而后聚焦在地球。从原始人掰下的第一块骨槌,到他们而今生活着飘飞在太空中的天宫号,‘弦乐家’好似对人类倍感兴趣。再之后是伏羲制琴的画作,是贝多芬肖邦的画像,是玲珑有致的编钟,是乐符翩飞的音谱,而后是钟子期与俞伯牙的高山流水,是一个万花筒,从四棱的彩色方形旋转重叠、跳跃,好似要在这二维的平面上展现一个三维甚至更高维度的世界,万花筒上的光斑斑驳闪耀,最后忽地凝成一个光点,镜头慢慢拉远,那是他的小屋,那是他横挂的窗帘,光点是阳光洒落遍地的万丛一点,他靠在床背上,出身地凝望着。不可思议的是,真空中漂浮的空间站里忽然向起了音乐,那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国际歌》!”他惊叹道,弦乐者不是毫无缘故的将他们拉出了风暴,而是他们的歌声拯救了自己。
在他们还在叙述这些细节时,地球的天空变了脸,不只是失去了星空,失去了原本的黑夜,现在的昼半球的天空也无比暗淡。“那是他们的全息投影。”宇航员们解释道。
一颗颗恒星被点燃,一颗颗恒星在闪耀,如同春日里一支迎春在微风里渐次展开的灿烂花蕾,灿烂而热烈我们看到的太空充满了欢快的音乐和舞蹈。不同的闪耀与亮度,不同的频率与频谱,是铺就在广袤的时空间中无数纵深的音符。行星的磁场也在这音乐声中共鸣,绽成阳光照耀下花瓣的身影,一串串一排排,那颗行星是桃花,另一颗如同海棠,还有绿叶一般的光在陪衬。
“难道这是对我们的恐吓?”“不!”一个简朴的衣衫站起身,公然打断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怀疑。“难道这还不够清楚么?他们没有敌意!他们只是在演奏音乐!”“你是……出现在白柱上的那个人?”“抱歉我不知道弦乐家为何会关注我,不过对我自己我还是清楚的,我的确经常望着地上的光斑出神,因为我想要做一个画家,却没有真正的自由去创作,您知道每天和一堆兄弟抢饭吃的日子吗?但我还是有这不切实际的想法,我是一个不合时宜者!当我看着光影在地上起舞时,的的确确,心里是响着欢乐的音乐,是口哨,是鸟鸣。”“您想要用这疯子般的发言说服我们?”“‘那些听不到音乐的人,认为跳舞的人疯了’,请您也听我说完好吗?”宇航员,她的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他和她一眼,说道:“从那边缘的意图展示后,那个白柱把我们的空间站包住,等到再次展开时,我们到了一个类似‘戴森环’的装置,白柱又向我们展示了一组画面——没有这个装置环绕的太阳再次星变,木星轨道内的一切都被膨胀的太阳吞噬,而有了这个装置后,他们仍旧要引发星变,却在离开后留下了一个完好无损的太阳。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弹奏恒星作为音乐,不过我认为,弦乐家是友好的。”“……您的经历实在是惊世骇俗,我们很难将这些话讲给别人。”“那就慢慢讲吧,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欣赏他们的音乐。”
尾声
松树下,他牵着她的手,望着慢慢掀开幕布的星空,看到夜空里几颗星星格外闪耀。“看,我们或许并不是他们的乐章,而是乐章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浪漫的种族,漫游在上光年的距离上用星星演奏乐曲。”“……嗯,或许,住在你的那个小屋就已经够了,不需要多大的大院子,温饱后,要多去看看星星。”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golden daffodils;
Beside the lake, beneath the trees,
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Continuous as the stars that shine
And twinkle on the milky way,
They stretched in never-ending line
Along the margin of a bay:
Ten thousand saw I at a glance,
Tossing their heads in sprightly dance.
The waves besidethem danced, but they
Out-did the sparkling waves in glee;
A poet could not be but gay,
In such a jocund company!
I gazed and gazed but little thought
What wealth the show to me had brought:
For oft, when on my couch I lie
In vacant or in pensive mood,
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
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
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村庄
小时候的村庄
夏季是麦子的芳香
我在玉米堆上跑上跑下
脚踝上的粘的须好痒,抖到地上
少年时的村庄
初秋的月光徜徉,银色落在无人的小径
田地生出排排高楼
我听到远方的火车呼啸,声音响彻远方
而今回到村庄
除夕夜的胡同黑夜的静谧
不再有户户红灯照在我的肩膀
彳亍的脚步迷蒙的彷徨
哪片云彩从来只属于一个地方?
转身回望,村庄只是变了模样
The Village
The Village,when I was young
In summer was filed with wheat’s fragrance
Piles of corn heaped on the basking field
Iswhere I run,shaking the scratchy silk onto the ground
The village when I was teen
In fall was the lunar grief lingering on silver lane
Rows of towers grew upon the land
Iswhen echoed the the whistle of a far away train
And now,,,,,back to my village
Silence soaked through eve of the Spring
No more red lantern glows warmth on myshoulder
Just with cold winds my legs changing
Clouds are all fated to wander,never tostay
Backwards,I see my village,just a oldfriend with a new face.
上一篇:征文 | 青春共话十九大——肖茁良
下一篇:【征文Show】| 当我在做梦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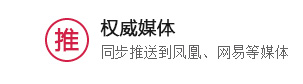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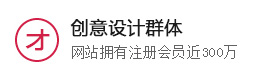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