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强震,持续时间约两分钟。69227人死亡,374644人受伤,17923人失踪,汶川之痛,华夏之哀。和大地一同震动的是心跳,震后余生,我们收集了关于那个在震前一无所知的小城,那些悲恸、遗憾却不曾遗忘的故事,新生不息。
罗星言
“那是一种让我几乎条件反射流泪的气味”
我的家乡在四川,08年地震的时候我四年级。地震发生后,所有同学起身离开座位往门口冲,我们班离楼梯口近,听到远远的有一群脚步声黑压压地往这边踏过来,原本安静的楼层听见老师们此起彼伏的“快点跑!快点跑!”的叫唤。
跑到操场的时候还不敢马上停下,又朝主席台最空的那片地奔过去。此时离感受到震动大概有一两分钟,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在几百公里外的北川都江堰,很多人在这一两分钟里,没能逃出来。
地震后我在外婆家住了很久。某天,外婆说要带我去看都江堰。我从未去过那里,只在新闻里看过都江堰一个又一个堰塞湖,知道它是重灾区。
都江堰进城以后,我看见被地震摧毁的楼房乱糟糟地倒在那里,东倒西歪的危楼外墙上写着红色的“危”字。路上人不多,至少电视里那些匆忙火急的救援人员已经不见了。天气炎热,刚到达的人们往城里走,少有人说话,只是看着两边楼房的残骸,像是肃穆地参加一场迟到的仪式。
再往前走,见到有一堆废墟格外高,比周围的残骸要高上好几米。外婆转过头问我需不需要口罩,我说不用,她说前面是都江堰的人民医院。我心里突然慌起来,走到的时候就后悔没有带口罩了。那种气味很难形容,早就听大人说过,但真实闻到的时候还是心里默念了一句,天呐。天气热得汗流进眼睛,我只想尽快走过这个地方,却还是在闻到气味的一瞬间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看到前面外婆好像也在哭。医院这个地点,在512这场地震里,让我们看到了太多故事,我当时只觉得,医院里没有逃脱的,是最无助的那群人,所以不敢再去想。
路过未倒塌的房屋残骸,我想起妈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她从前当兵的战友在都江堰工作,地震来的时候刚跑到一楼只差一点跑出去,楼就塌了,人没了。其实我见过那个叔叔,喜欢了我妈很多年,直到去世前都是单身。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把我爸给我买的凉鞋扔河里然后带我去买了双新的,还买了新的衣服和裤子。当时我自然什么都不知道,大人们不会去说,小孩子自己琢磨。我沿途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想着哪一栋楼压了他?这些路过的楼房都压着谁?他们牵挂谁又被谁所牵挂?
回来以后很长时间我试着不去回想那座城市里我所看到的景象,还有那种让我几乎条件反射流泪的气味,我不去想那些被埋者的故事,也不再猜测楼房瓦砾曾见证多少情感。
10年后再回望,心里依旧是难受的。人一旦经受过在强大事物面前的无力感,对这个世界便少一分强求。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曾在灾难中看到那样多人性的光辉,灿烂的故事,心存过往的依旧在铭记,温暖动人的依旧被怀念,而今即便是这样的灾难后,我们也一定可以不服输地说,我们并不是一无所有。
朱迪
“一肚子的遗书,都成了对着天空许的愿”
我打了同桌一下,呵斥他干嘛又踢我凳子,直到班主任冲进教室叫我们快跑的时候,我仍觉得是一次演习。
整个小学的小孩儿和老师都跑到了操场上,我傻不愣登地站着,原来刚刚在楼梯间跟着飞快往下冲的时候,脑子里已经对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轻轻地告了别,然后挤出了一滴泪。
我想也许是过了很漫长的时间——老师的电话被打爆直到彻底没电,陆陆续续有家长夸张地跑来扑到自己孩子身上,有的女孩儿在偷偷呜咽,还有的小孩儿聊着乱七八糟的话题打发时间。
教学楼被封锁,校长在主席台上声嘶力竭地安抚大家的情绪,老师在一遍一遍地清点人数。五月的太阳已经有些灼人,我被晒得脑袋昏沉失神,索性坐下来开始思索遗书要怎么写。年仅十岁的我,在那时发现自己多么地一事无成,也发现自己有多么爱我的家人。没有笔和纸,一肚子的遗书,都成了对着天空许的愿。
身边的同学慢慢被接走,虽然知道我的父母工作单位离我的学校很远,但我一度怀疑他们可能已经“遇难”,甚至要老师带着我上楼拿自己的公交卡和家钥匙,决定像往常一样自己回家。我的视线里,大楼没有倒塌,大地没有开裂,没有人流血,我以为这只是一场小小的震动而已。
带着劫后余生的欣喜回家打开电视,才错愕地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如何降临到你的故乡——四川大地。晚餐时和家人交流整个下午的遭遇,在庆幸,却是沉重地庆。彼时的我很难想象,震中现场是一幅怎样的景象。电视里报纸上铺天盖地的黑白色新闻,令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人间的图景。
接连两晚,我们家都带着必需品,把车开到平坦开阔的地方睡觉过夜,那盏路灯应该听见了很多我们互道的爱意。
(摄于汶川大地震纪念馆)
直到前年从西北自驾回来路过时,才有机会去了汶川大地震纪念馆和映秀中学旧址。对面山腰的公路上仍是处处被泥石流彻底阻断的样貌,山体还有部分裸露的岩石,脚踩瓦砾,满目狰狞。
过了这么多年,自己都没想到的是,我也会在纪念馆里崩溃落泪。人的面孔,县城的面孔,自然的面孔,以及无数个摇晃和破碎的时刻。或许是那时刚刚填报了新闻专业志愿的缘故,看到记者们留下的印着各家媒体特制的T恤和记录视频,无力感被拳掌间涌动的一股力量打破,“有些笑容背后是紧咬牙关的灵魂”。
第二天在路边一水果摊准备买些当地李子,渐与摆摊的小伙子攀谈起来,他说起那场地震,说起如何失去亲人,四肢皆成异形无法用力,后来在帮助下走出阴霾,现以买水果为生。看着他黝黑年轻的脸庞,我不知道他匆匆带过的“从地震中走出来"的心理意志经过了怎样的跋涉。他的手心紧紧地攥着,一边说着感激的话一边鞠躬。
我们知道“众志成城”的口号声浪下实情数据的刻意隐瞒,我们知道人心的伤痕不会像“新的家园”一样没有痛苦的痕迹。追问预警和应急预案,追问救灾主导者角色的缺位,追问难以启齿的“豆腐渣”之痛,追问灾后重建的粗暴和失节,追问一线信息的扭曲传播,都是为了让今后无法避免的自然灾难的后果尽量减轻。
五月应该是悲哀而清醒的。“重新开始”一定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但在更广阔的背景里,他们的十年,也是我们的十年。未来若仍有不幸降临,还会有这般惴惴不安吗?
任君
“一只老鼠活蹦乱跳地从水泥板下跑出来出来,都能让我们欢喜”
我的家乡-德阳绵竹,属龙门山断裂带,地震极重灾区,一个因人杰地灵而有着“小天府”美称的小县城在一夕之间,轰然倒塌。
那个压抑的午后,出奇的阴暗,晌午刚过,云层便已沉顶,还记得出门前,隔壁的阿姆还叫喊着叮嘱自己即将外出的女儿:“阿囡,带把伞,要下雨咧——”,长长的调子拖出满满的爱意。没成想这一走,便是天人永隔。
14时30分上课,我一边反复地看手表,一边烦躁地跺脚,急匆匆地跑向学校。当指针指向14时28分,突然听见从地底传来的巨响,一种轰隆隆似拖拉机驾驶的声音,持续大概5秒后,地面开始晃动。
起初,动静不大,部分建筑物“从天而降”,那是碎裂的混泥土砖瓦,大块大块往下掉,砸中不少行人,血迹斑驳水泥路面。几秒后,大地变成了一艘风浪中的小船,开始上下晃动,左右摇摆。呆愣在路边,八岁的我被狠狠地甩向一边,紧紧地抱住树干,不知所措,无法言语。幢幢高楼,轰然倒下,废墟和灰尘恶灵般席卷全城。
一瞬间,传来万物嚎哭,哀叫,可是下一秒,寂然无声。夏日的蝉鸣,蛙的聒噪,雀的咕叫都顷刻消失。在地震暂停的喘息间,才发现,所有的动物都没了踪迹;才发现,我们的渺小,人类的迟钝。那是我迄今都不愿想起的寂静,那是惶然的气息,绝望的味道。
本能牵引着我跌跌撞撞地扑向学校,老师呢?同学们呢?食堂的叔叔阿姨们去哪了呢?眼前只有废墟,连呼救声都微不可闻。木然的我踉踉跄跄地又往家跑。一路上,有抱着满脸灰,早已没了声息的儿女的母亲,有托着自己残肢一瘸一拐的工人,还有跪在废墟前悲痛欲绝的父亲……
震后,大家凭着一丝丝不甘和渺茫的希望,日复一日地撑着,在废墟中找寻着力量。甚至有时候,在救助时,一只老鼠活蹦乱跳地从水泥板下跑出来出来,都能让我们欢喜。
提及当年,我们有的不只是悲痛,更多的是感恩和坚强。我们珍爱生命,感谢身边人的陪伴,感激他人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
艾杰
“遍地都是伤者和死者,我的伤在这里根本微不足道”
地震发生那年,我正在绵竹市汉旺镇中心小学读五年级。
当时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地震发生时,我正在讲台上组织同学们午唱。突然摇晃起来,大家都一窝蜂的往外跑。楼梯是在教学楼的两边,我的记忆止步于我跑出了教室到了楼梯上。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就像一场梦睡醒了,我发现自己全身动不了,呼吸也很困难。两位好心人把我从废墟里救了出来。
爸爸妈妈当时在汉旺镇上做生意,而在地震发生后,他们第一时间到学校来找我。妈妈在看到我之后,想冲上废墟来找我,然后穿着高跟鞋走不来,她就脱下高跟鞋,光脚爬了上来。因为惊吓过度,我迈不开步子,爸爸将我从废墟上背了下来。当时我头部受伤,左眼受伤,还有锁骨骨折。爸爸先骑着摩托车准备带我去绵竹市里找医院,到了县医院和中医院却发现遍地都是伤者和死者,我的伤在这里根本微不足道。
我和妈妈在爸爸朋友家附近安顿下来。我因为脸部的疼痛,除了喝水,什么都无法吃。第二天早上,爸爸继续出门给我找药,找医生,却依然没有收获。从事情发生那一刻起,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可是在爸爸回来告诉我还是没药的时候,我哭了出来。后来,体育中心一位从外地来支援的医生为我处理了伤口,我的头被缝了二十多针。
因为我受伤了,家人都在陪着我治疗,只有爸爸偶尔回去过一次。爸爸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店里、仓库里、家里的东西都还在。可是过了不到一星期,爸爸再回到汉旺的时候,发现店铺,家,仓库,全部都被洗劫一空。我爸妈在汉旺做了十年的生意,那是他们十年的积蓄。
爸妈当时什么也没有说,直到我完全好了之后,他们才告诉我的。爸妈总是安慰我,钱没了我们可以再挣,人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地震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爸妈从头开始做生意,我劫后余生,相当于重获新生。直到现在,我仍然很害怕突然的喧闹,怕去人多的地方,怕很安静的时候突然有人喧哗。我会觉得,是不是又地震了。这种恐惧可能是我这辈子都克服不了的。
这十年,我从小学到初中,考高中,上大学。经历过地震的我们,可能更加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也更想用有限的生命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一钦
“那是一种极其恐怖,如高压电流般的力量”
成都主城区距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镇仅73km, 但地面烈度只达到了5—6度,几无建筑破损,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地震来袭时,成都是相对稳定、安全的。但当时的震感和恐慌,依然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事情发生时正是体育课,我们都在操场上。那一年我八岁,脑子里根本还没有地震的概念。后来我常常想象,如果,当时我在教学楼里,会不会害怕地忘记逃跑?会不会被同学抛下?会不会一个人穿梭在摇摇晃晃的黑暗长廊中?
地平线在不停地上下晃动,整个世界仿佛要开始颠倒。比起恐惧,更强烈的是震撼和好奇。我蹲下来,用双手撑着地面,地底深处的巨大震动自手心传来。那是一种极其恐怖,如高压电流般的力量。
班主任告诉我们汶川出事了,很多人一下子就哭了。有人说自己的姐姐现在在汶川生死不明,前几天还在成都,要是晚点回去的话……有人说阿姨,有人说舅舅,有人说自己的外公外婆。不管是多远的亲戚,讲述的人哭,我们也跟着哭,每个人都努力地搜寻着汶川与自己的联系。
之后的一次余震,我正在睡觉。妈妈突然敲我的房门,说地震来了。我瞬间清醒过来,四处找裤子。我一时找不到,急得要哭,就拿起一条家里的毛巾裹住往外冲。我刚跑出大门,地震停了。妈妈笑我胆小,我却一下子失控地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那种濒临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存的渴望,以后再也没有那般强烈过了。
震后的十年内,成都市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一系列防震演练。2013年的雅安芦山地震,我所在的树德中学的师生,从教学楼撤离到操场,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彭栩
“没有少儿频道的黑色日子”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绵阳三台,属于灾情较为严重的地区,那里距离震中汶川较远,但地震波在地面上留下的痕迹和心中的印迹同样深刻。
当时正是午休时间,当我走下讲台到自己座位取物品时,突然间感到背后遭到人重重一推,我以为是后桌同学开的玩笑,但回头一看发现同学依旧沉浸在睡梦中。刹那间,楼道里传来了惊惶不已、轰鸣震耳的脚步声,尽管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本能地叫醒同学,带领他们冲出教学楼,随着学长们一起来到开阔的操场等待老师的到来。
当时我并没有感受到特别危险,在冲出教室后没有去找老师,我站在操场上望着教学楼背后的山,望着天空的远处,我以为天上会有什么奇异的东西掉下来,是外星人入侵还是战争的轰炸机飞来?等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我才从脑子里搜索出依稀在新闻里听到过的一个词“地震”。不是很清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什么,又会带走什么,只知道是灾难。
因为离震中距离较远,学校并没有发生房屋倒塌的情况,大家都相安无事,只是两个可爱的小表妹在旁边泣不成声,“家里的老房子已经很旧了,婆婆爷爷还在里面呢......”
那天下午,在紧张的等待中,时间仿佛过的格外漫长,与其他同学相比我感到自己的家长来的是那么的晚,父亲带我回家取避难物资。现在我还清晰地记着狼藉的家中,冰箱和立柜式饮水机都倒在了地上……而当我踏上老屋院子里的阶梯时,一阵地动山摇让我站不稳脚跟,良久方才平静,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场5级的余震。
为防万一,父亲决定带全家人晚上先在面包车里休息,蜷缩在停于操场的面包车中,那一夜显得格外漫长。第二天,亲戚送来帐篷,政府也派人分发粮食、水和生活用品,那长期扎营操场的生活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经历。
后来的十年里我一直生活在经历了地震的小镇,除了乡间陡然林立的复合楼房,那里变化不大。只是此后一两年,坐在车上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震后的小轿车越来越多了,钱留着干嘛,不及时行乐,怕某一天人走了钱没用完,多不划算。
那次地震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教育,告诉我们生来就在一个地震频发地区,除了积极防灾抗灾,要做的大抵是对身边的人更好些,因为想着说不定某一分钟之后,在乎的人就消失不见,用尽力气也挖不出来,就永远埋在废墟之下,从前不愿意听的话再也听不到,从前不愿意多说的一句话再也开不了口。那是一段没有少儿频道的黑色日子,电视上嘈嘈杂杂的全是关于灾情的报道。
整理丨记者团 付蕾 汤子凡 李梦琪 王一钦 张东琪
图丨记者团 朱雯卿
编丨记者团 张梦洁
上一篇:《有奖口号征集》家,一直都在……
下一篇:【公示】快来看!枞阳旅游宣传口号·形象标识(LOGO)入围名单新鲜出炉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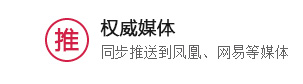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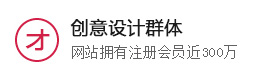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