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
如果家乡的名字都被改得面目全非,
那还是记忆中魂牵梦绕的故土吗?
2013年,湖北青年葛宇路刚来北京,住在城中村。行走在京城各处,打开地图软件,遇到无名的小路,这个热爱行为艺术的年轻人就把自己打印的路牌贴在那里。
有一天,葛宇路的一个朋友叫外卖,把手机地图放大又放大,忽然发现“葛宇路”三个字赫然其上。这是葛宇路的名字,也是葛宇路给这条小街道起的名字。
被地图软件收录进去,葛宇路对“葛宇路”也认真起来。他专门做了一块写有“葛宇路”的路牌,和正规路牌的外形尺寸一模一样,然后和朋友一起把牌子有模有样地竖在路边。
这时候他并不知道,这条四百多米长的小路,早在2005年就被命名为“百子湾南一路”。当然,管理部门也不知道,有个年轻人悄悄地给这条街道来了一回二次命名。
葛宇路路牌。
后来,葛宇路上了中央美术学院,2017年,《葛宇路》被他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一篇《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命名的路》文字也在网上流传。很快,印有“葛宇路”的牌子被清除了,“百子湾南一路”的路牌竖了起来。
风波之后,葛宇路对媒体说,有时在北京他看着那些亮灯的人家,会幻想有一间属于自己,他的行为是希望人们对于地域和个体身份有更多思考。这次事件引来了公众对于地名变更的一场讨论,不过,类似的讨论,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
赋予一块土地以名字,相应地,这个名字也成为人们归属感的具象化存在。每一次修改地名,无疑都在稀释这种归属感。2010年,千年历史的北京宣武区被划入西城区,这也才有了后来电影《老炮儿》里那句对白:“六爷,没宣武区了。”留下镜头里的角色们对着胡同发呆。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修改地名?又该由谁来以何种方式改名?这么多年,中国人看惯了五花八门的改名,但还是没怎么想清楚这个问题。
更换的百子湾南一路路牌。
套路一
从土气到洋气:没人要的名字,我拿走了
在郭敬明的大作《爵迹》里,既有天束幽花、鬼山莲泉这样带点东方风味,却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角色,也有特蕾娅、漆拉这样满满西式风情的名字。如果地名也如法炮制,将土里土气的旧称变成带点翻译腔的新名字,仿佛整个城市都在一夜之间洋气起来。
其中的典型要数香格里拉。
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描绘了一个东方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但这位作家万万没想到,许多年后,中国的几个地方会因为这个小说里的名字展开一场争夺。
原上的香格里拉,原名中甸。
最终,在1997年,云南中甸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香格里拉就在迪庆。之后的2002年,正式举行了更名庆典,中甸县改叫香格里拉。
与之类似的还有湖北仙桃。当初,上千年历史的沔(mian,三声)阳县,摇身一变成了仙桃市。原先的名字生僻,新的名字好听又好记,可直到如今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一个不产桃子的地方,怎么就被叫做仙桃了呢?是谁定下这个名字的呢?
看上去改得更好听、更洋气的名字,更像是无根之木,很多时候没法得到所有人发自内心的认同。
套路二
拼历史:越老的名字,就越是好名字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葛剑雄曾在一篇题为《更改地名之忧》的文章中批评道:“有的地方一味复古,非要采用最早的地名,以显示本地的历史悠久,却不顾这个地名与今天行政区划间的明显差异,实际影响了对当地历史的正确理解。”
2010年,原襄樊市终于完成了它更名襄阳的夙愿。
满打满算,襄樊的名字只用了六十年,和襄阳二字的历史文化积淀相比,似乎微不足道。时任襄阳市委书记唐良智表示,襄樊更名为襄阳,是尊重历史、传承文化、顺乎民意之举。但地名不是说变就变,这次更名的代价,着实不小。
在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襄樊改名襄阳,襄阳区改名襄州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修改。从世界地图到区域地图的改版重印,市、县、区、乡、镇各级单位的公章变更,路标、牌匾还有户籍、证件的调整,据媒体事后估算,这个过程产生的成本可能上亿元。
很快,火车站候车大楼上原本矗立着的“襄樊”两个大字,也变成了“襄阳”。过去的名字还要一段时间才被遗忘,新的名字还需要人们慢慢适应。恢复了更具历史气息的襄阳,是不是就能重现往昔的繁盛呢?时间会给我们答案。倒是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总有外地人一不小心把襄阳叫成襄樊。
后来,有网民趁热打铁,呼吁把湖北省的简称“鄂”改回更有底蕴的“楚”,没有得到太多响应。理智的人都明白,单单是把全省境内车牌上的“鄂”换成“楚”,就不知道要付出多高的代价。
套路三
蹭热点:什么出名,我们就叫什么
今年五月,安徽宣城主城区四条道路,准备以本地盛产的文房四宝命名,引起很大争议。
在更名公示里,当地政府给出的四个名字分别是宣笔大道、墨香大道、宣纸大道和宣砚大道。通俗,直白,极富冲击力,宣传本地名产的热情一览无余。
不过很多市民并不买账,他们坚持认为原本的宝城路、薰化路、响山路更有韵味,比这些浅白近乎于广告语的新名字好得多。当地政府宣传本地文房四宝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直接把“笔墨纸砚”四个字嵌入名字的方式,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
本地有什么名胜、名人、名品,发生过什么著名事件,只要是能提升知名度的,统统可以用来改名。
比如湖北的黄冈和咸宁就争夺过古赤壁的归属权,两市还为此组织专家论证。最终在上世纪末,咸宁市下辖的蒲圻更名赤壁,这场争论才算结束。
更为人所知的改名是安徽徽州为了突出旅游特色,把名字变成了黄山。三十年前,地级黄山市正式成立,《牡丹亭》的作者、明代文学家汤显祖的那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一时没了着落。
后来,改回“徽州”去的呼声不绝于耳。《人民日报》还曾写道:“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毕竟,没有‘徽’,哪来‘安徽’?”今年年初,面对再次改名的声音,黄山市政府在官网发文表示,无论是否复名徽州,徽文化都会传承。算是暂时给争论画上一个句号。
闻名中外的徽派建筑。
以点带面,试图以区域内最有名的事物来带动整个地区的知名度,这样的命名逻辑,很可能弄巧成拙。2016年,陕西勉县撤县设市,勉字是不能用了,于是向全社会征集名称,其中“定军山”的名字最惹人注目。
类似的,还有将贵州仁怀市改为“茅台市”,将河南鹿邑县改为“老子县”,贵州水城县改为“夜郎市”等等提议。
名山名水名人典故似乎是产品商标,只要下手够快,就能提前抢注。只是这样兴师动众,真能争取来最大的地区利益吗?还是要打一个不小的问号。
套路四
无中生有:这世上本没有名字,
但我可以新起一个
2016年,来自郑州的一次有关命名权的争夺引来媒体的关注。
一方是丁楼村的村名,希望新地铁站定名为“丁楼站”,以让后辈记住他们已经拆迁的丁楼村,另一方是河南工业大学,认为地铁站以大学命名理所应当。
最终,河南工业大学胜出。有些不甘心的村民把印好的丁楼站的贴纸贴在建好通车的地铁站,但这场争论已经没有了悬念。这些或主动或被动完成城市化的村民,想在一个新名字里保留他们村庄的痕迹,有村民对媒体表示,他们甚至接受“河南工业大学丁楼”的名称,终究于事无补。
这样围绕地铁站名字发生的争夺不止出现在郑州。如果一个外地人来到广州搭乘地铁,一定会被一些站名搞晕:京溪南方医院,嘉禾望岗,南村万博,汉溪长隆等等。如那位郑州村民的设想,这些新名字都是由两个地名合并而成。虽然初听上去怪怪的,但是避免了地域之争。
有些新地名是在原有名称基础上修改,有些则是完全凭空创造。不信你打开地图看看,全国有多少建设路、香港街、中山大道、光明大街?随着新建城区扩大,各种各样一言难尽的新名字冒了出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恐怕就是“地产体”。
为了把房子卖出去,地产商可谓挖空了心思。观澜豪庭、临江公馆还算是含蓄的,意大利花园、罗马假日、巴黎印象、香榭丽舍嘉园了解一下?不土不洋,不中不西,走进中国大小城市的新城区,沿途所见都是乏味而突兀的名字。
人如其名,从某个角度出发,也可以说地如其名。一个人改名都要格外小心,何况地名呢?
此前,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就表示,要坚持“地名要保持相对稳定”原则,格外慎重。《人民日报》也曾经刊登一篇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文章,其中强调:“地名的替换与取消,显然需要慎之又慎。”
过于草率的频繁更名,显然是一种短时行为。少小离家老大回,如果家乡的名字都被改得面目全非,那还是记忆中魂牵梦绕的故土吗?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平台新周刊(ID:new-weekly)
值班编辑:韩忠强
▼
推荐阅读
我宁可排队等吃饭,也绝不自己下厨做顿饭
1966年,傅雷夫妇自杀,三个人的命运随之改变
央行和财政部“互怼”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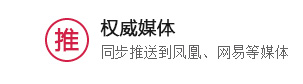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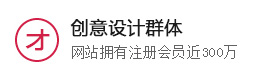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