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在齐家坪,与岁月长谈
甘肃 孔令莲
齐家文化是以中国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时间跨度约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4省区,因1924年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首先发现而得名。齐家坪遗址是黄河上游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存。
广河县
隶属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广河县,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为大夏、诃诺、木藏城、定羌、太子寺、宁定、广通,这些名字一经说出便如同天启——这里寄存着先民黑色的眼珠,印着大禹沾满黄河水的泥脚印,是先民用陶片缝制的外衣,一寸一寸包裹这片黄皮肤的胴体和乳房。
广河,东有洮河水环绕,西有大夏河、广通河,南接茂密的太子山森林,这么多的水聚集在一起,与这片博大的土地相遇,恰好有一些闪着青铜之光的思想一点一点浸润瘦枯的生命。这片沃土,必然会孕育出世间最完美最圣神的历史传奇。
齐家坪遗址的威严和震撼在于荒芜与焦渴:随处可见的碎陶片丛生在大地上,一片一片犁开远古的烟火,从繁华到静寂;古城厚厚的城墙,负载千年风雨,究竟顶住了多少回泥沙俱下的扑打和顶撞?火坑中似有枯木正在熊熊燃烧,铸造一个王朝的玉玺,举起第一个部落联盟的王朝——夏;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在这里交接,开启中西文化交流与渗透的大门;古文明的传播和流动在这里中转休憩,为群峰、黄土、玉石、丝绸、飞天打开悟道的法场。
这片热土,是华夏文明的根部和渊源。我看见:华夏子孙循着汤汤流水落地、长大;华夏文明沿着滔滔黄河水,汩汩淌出夏、商、周……
远古的齐家坪应是一片海,或是一汪巨湖。夏日,风雨叩石,黄河、湟水、洮水、广通河水汇集于此,浩浩浊水低头俯冲,乍回头,漩涡飞转,汪洋泽国,洪水掀起层层巨浪,扑上来,又扑上来。洪水所到之处,淹没山陵,摧毁窖穴房屋,吞没黍粟,人民流离失所。河岸川台的人们,一步步后退,再后退。这些铁马冰河的流水,能浇出丰茂植被,推出肥沃土地,也可以瞬间使河流纵横,湖泊星布,还不忘时时发发温柔的坏脾气,让沿河两岸家破人亡,沧海桑田瞬间交替上演。
远古的水,是齐家坪川台上流动的野性诗歌,喜欢在皇天后土中疯长。万道霞光中,我看到百鸟聚集的翅膀,水草丰茂的腰身和容颜不老的胭脂,以及刀劈的、陡峭的、连绵的山峰,迎着太阳起起落落,描摹斑驳间掩隐的亘古和细碎中潜藏的久长。
大禹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一种亲切,隔着往事,直往心里钻。那些石斧、石铲、石锛上印着的呼吸还在沉睡,相隔千年宛如初见。共饮一江水,就连乡音都是天然的味道,带着粟黍的清香。如果我们迎面走来,你的举手投足和我沾满呛人黄土的乡音俚语,定会一见如故:这壶老酒,怎么喝都会醉!即使此时,我独自臆想你,字里行间写满的都是你胸中的风起云涌和脚下的千古回音。
在导通龙门的那一刻,你目送滚滚流去的一江水,会不会像我这样在你站过的岸边,因执念破壳而潸然泪下?鲤鱼跳过龙门,便是通达河州,是流水三千的江湖,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一步跃出去,便是天地间奔流到海不复还的天之涯,海之角。
埋下铜斧、铜镜、陶和旌旗、兽骨,以及一场狩猎的奔跑、呼喊,看看栅栏中围着的猪、羊、狗、马,试着豢养一只鹰,模拟鹰隼起飞的姿势,偶尔仰起头接收鹰眼里蓄集的闪电和不灭的火焰,不忘尝试和鹰对话、交流。
那一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田之罚”——驯服大河的禹再次开口:出征必将是“除天下之害”。大夏的烽火第一次被人燃起,天底下的事、物即将有序有理有据。大禹伫立龙门,满眼是大清大浊的黄河,龙门之外的丝绸、茶马、漫漫黄沙,以及紧锁的玉门即将铺开八千里路云和月。那天,禹立在大地上,天空比他高一些,他的召唤比大地高一些。士气熊熊,群雄争霸,舍我其谁?尧舜禹伐三苗的战争,以黄河流域部族集团的胜利,逐渐催生一只燃烧的苍鹰——大夏王朝。
古道热肠,一瓢黄河水足以醉倒万里沙尘。唯有大禹有幸踏遍无数江山,那些逆风雨而行的碎步镶嵌在《史记》中,密密麻麻的汉字都是手握石铲挥锤治水的身影。也许,那个端坐称王的大禹只是历史中的逗点,却将中国汉字分段排列,层次分明。汉字至今沉默,却胜过千言万语;大禹至今沉默,只有大河昼夜代言,亘古不息。
风不说话,我一动不动,任凭思绪自由游荡,游荡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大夏古城。合着布谷鸟、蟋蟀的歌唱,我有一千个理由相信:羌人故里,大禹的古城岁月,每天都是黍粟进仓,家家煮酒。好酒入喉,人们迈着虎的步幅,来回丈量黄土大地上自己的家园,以鹰的表情俯瞰山川,在黄河水中把“规矩”、“准绳”洗了又洗。
铜镜
岁月恰好达到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大河汤汤,情怀不绝;大山矗立,静默不语。这是父性和母性的融合,雄奇与柔媚的交汇,大地上孩子、羊群、菩提、眼泪,以及黍、粟、山桃、野杏和葵花一起出生,成长。
一眼千年,轰然打开这本时间之书,双耳罐、大口瓶、乌形壶拨开千年云烟,踩千层厚土滚滚而来,微微睁眼启唇,诉说先祖窑穴中常年不灭的火种,叮咚脆响的玉牙璋上雕刻的威仪,和上通天下接地的炊烟。
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大禹顺应流水以导河。埋藏在时光深处的寒波,遮不住玉石被淹没的温润。以礼器飨天地、神灵、先祖,磊磊玉石铺起的大路上,星起星落,蛐蛐翻墙,九月的野狐眉挂白霜,为身背箭袋的祖先镶嵌路标。箭未出鞘的祖先,双手接住头顶划过的闪电,和黑夜中滚下的雷声,那一刻,他是天地间的王。
绕过陈旧,沿袭昨夜的漫天繁华和一袭长梦的思绪,把一些思绪浸到脚下的河水中漂洗再漂洗。抓一把火种,摁进月色漂净的乱石中,冰凉的胸膛里,定会淌出一串串滚烫的藤蔓。石破北方而启生:将一江秋水翻手浓缩,或将晴空明月的样子浇铸成一柄铜镜——这里的另一个我,在黑暗里等待被发掘照亮!
惯于烧陶冶铜的黑眼珠,第一次在铜镜中端详、辨认自己,禁不住轻轻问一声: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端着镜子里的自己,虽生死缄默不语,但所有的惑已开了悟,遮在眼前的迷雾随铺在河面的根须流去,去往更高更阔更宏大的远方。
一柄满载顽石憨态的铜镜,开眼的一瞬间,就泄露了一个王朝的一言九鼎。红铜、铅青铜与锡青铜的厚重坚硬,麻丝经纬交错的编制,足以遮挡千年风吹、万年日晒。时间一样长的灯芯,老井一样满的油灯,照亮的不再是清瘦的石器和素陶,还有锐利的骨骼在铜镜以外继续酝酿的另一幅五官,譬如通铲,铜斧,铜剑,以及比铜还硬比水还软的思想——只有这把铜镜有幸让你发现自己,世间不再只是堵在眼前的你和江山。
铜镜,记录着光阴似箭,也洞晓岁月无边。
需要多厚的一片黄土,才能承载起华夏民族最初的文明星火?让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半山文化的种子如此集中栽植在甘肃大地上?这脚下低眉顺眼的河流,笑靥间弯出的轮廓里,满是仓颉造出的横竖撇捺,黄土高坡上,刻满西北风低吟的唱词,柔软如丝绸的飞天里,窜进一些飘逸的篆意简味。
这面站立在远古人影中默不作声的镜子,照见日月之外自己的那一刻开始,先祖的长夜随即变得短了些,白天变得长了些。
粟
水道弯曲,绿树有影,天上百鸟欢歌,沼泽地里天鹅惊飞,天空划过一道闪电,随即响过一声春雷,天地翻身坐起揉着惺忪的双眼,一一苏醒过来。同天地一起苏醒的还有稷,即粟,适合在干旱、缺乏灌溉地区生长,有白、红、黄、黑、橙、紫色,所谓粟有五彩。黄河、洮河、广通河所经之处的滩涂大地,恰可遍植粟。
石臼捣舂,就可饱腹。
粟,虽然颗粒细小,可一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千千万万粒粟脱了壳就是美食。时至今日,黄河沿岸的人们一直沿袭粟的食用:大病初愈的人或刚刚生产的妇女,每天一碗热乎乎甜丝丝的小米粥,谁都知道这是最好的调节肠胃的大补食品,是深谙粟之脾性的厨娘惯用的吃食。
粟文化里,汹涌着大夏漫山遍野的草籽和一抔黄土,指间擎起的是绵醇的琼浆。九州大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狗儿吠,牛马跳,栏内猪羊嚼嫩草,这是祖先的遗风,也是后嗣的沿袭,至今不绝。
弯腰是祖先血液里流淌的虔诚,大地定会成全一束粟穗饱满的风骨。从此,种子撬开大地的胸膛,铁骨似金,婉约如兰,一束粟决心养活一季沧桑。粟把晃眼的湖举上天空,落下来,使一道峡谷旷达,顺手抽掉高原骨骼中渗出的寒凉。大地不再沉默,比粟粒细小的诉说堆满谷仓,使人们拐过河流的弯道时在夜风里飘起来,再稳稳地落下。
黄河,飞翔的水,藏掖蓝色的翅膀。流淌的是鱼虾、飞鸟、寒鸦,还有一些根须飘飘的思绪,它在一些人的胸膛里孕育发芽开花,浇灌出果实和种子。
漫山遍野中站立的粟,细嫩的头一探一探顶住黄土地上来回的脚掌。他们,听得清种子发芽的声音,读得懂种子的心事。大夏城外,慢慢咀嚼一口粟的香甜和山头上喊出的第一声高腔,定会让奔跑的河流回头,又回头。
渐渐远去的不仅是窖穴黍粟,还有黄土掩盖的半亩大夏时光。一声鸡鸣,点亮大夏古城,猿啼、鸟叫、狗吠、蛙鸣,细细碎碎的声响填实火塘里的烟火,和热气腾腾的粟食。
后羿留下的最后一团火球,适时唤醒漫山黍粟和山桃野杏,以及四季更迭的齐家坪。这里的黄土中,沉睡着一部飘着酒香的慢时光。
与岁月长谈
暖烘烘的黄土大地,微闭双眼全身心沉浸在这片旷野,浑然进入某个俄罗斯画家的油画中。夏风吹来,有远古的意味。田间麦地,行行麦芒如针,无畏成长;队队苞谷树,如列阵士兵,养精蓄锐;白花蚕豆,紫花胡麻,红花洋芋,都蓄满独立昂扬的生命幽思。
时空旋转,飞逝如电,我是黄河岸边齐家坪古城中走失的那个孩子的子孙,我的五官间隐藏着祖先不灭的记忆。风,吹乱长发,我黑色的发丝里浸满关山苍野、植被盛大的黄土地的气息,那里种满祖先的骨头和卜辞,还有一茬比一茬饱满的黍粟。汹涌来去的浪花,一波一波打湿乡愁单薄的衣襟,谁都知道,乡愁虽然会在深秋里越来越老,但世上的乡愁怎么写也写不出斑驳的味道,那里住着一部浩大的童话。一些诗歌翻卷着翅膀掠过,像母亲跌落的牙齿叩击大地——这些隐匿在脚下的暗喻,风不知道,我知道。
当一艘货船的汽笛声,撞疼蓝色河流的肋骨,阳光如词,朵朵浪花排队列阵,连缀日月星辰,祖先光着膀子开始在羊皮筏子上歌唱,在远古的光阴里和我侃侃而谈。而我,怀揣佛的执念,任由门址、墩台、石城墙逐一开口,说出上古的一日时光:在诸神点亮灯火的山路上,导河的大禹和部落联盟“禅让”的大夏便浮现在眼前,我用祖先赐予的双眼一遍遍触摸大夏古城的荒冢和白骨,直到泪流满面。不远的田野,正好麦穗灌浆,蚯蚓犁地,獾猪夜行,萤火虫点灯,一些诗歌乘着风的翅膀踏月归来,任佛光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把六字真言念了一次,又一次。
我情愿此生,就这样跪着和岁月长谈:风从做旧的远方奔来,带着一座城池的遗味,先祖干净的面孔,黑色的双眼,随风潜入五脏六腑。仅仅一个眼神的长度,岁月就让齐家坪的每一束光都披上丝绸的火焰,温暖每一株花草藤蔓,照亮天地人间,以及在田地上行走觅食的生灵万物。
万物美好,我在其中。大地如此安详,一些写意的山水,用丰盈的身子背起后世子孙的烟火日子,搭起通往彼岸的渡桥。
2018年3月24日 孔令莲
上一篇: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优秀征文展示:《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下一篇:润·征文|“黄金视力眼贴·润故事”征文大赛启动,等你来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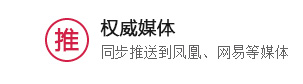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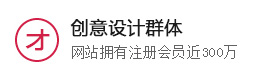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