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那口老井
付谦
每当杏花飘飞的季节,我就更想念一个叫小谷坨的村庄,小谷坨一个古老的地名,豫北偏僻的小村,闭上眼睛,就能唤醒我十三岁的记忆,村南一片杏树,村东一口老井,而清明唤醒一处的记忆,又会连带多处,最深的记忆是母亲与那口老井。
一九六九年11月27日,我们全家迁徙到这个小村,借住在村南一户农家柴房,里面仅有一盘塌陷的破土炕,破木门手指宽的缝隙,寒风来去顺畅,窗户是一尺大小的洞口,外面用草帘挡风,村里没有通电,照明是一盏油灯,一只木条包装箱,一个煤炉和一口水缸,则是全部家当了。面对昏暗的油灯,我天真的问母亲;“妈妈,明天我们能回北京吗?”,母亲没有立刻回答我,坐在那里发怔,眼圈泛红,我似乎明白一些。
家有了,先需要饮水,母亲向房东借了水桶和扁担,带着我去那口老井挑水。从我家到村东,要走过两个路口和一座池塘,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得很慢,似乎在努力记路,或若有所思。这村实在是有年代了,破旧的土房,那棵嶙峋老树与条石堆垒的老井,因为各自的年代和体量而互相矜持,对我们突然到来,也没存偏见,结果,渐渐熟悉走到一起。踏上满是冰凌石阶才到井口,我是第一次见到汲水的铁辘辘,辘桶上盘着很粗的牛皮绳,绳头拴着一串葫芦环,闪闪发亮,怎样用它锁住水桶?路过的老乡教会母亲,于是,井台叮当做响,一片热闹了。回家的路对母亲很漫长,一挑水压着瘦小的身躯,晃晃悠悠,步履蹒跚如那个时代,我想试试挑水,但被母亲拒绝,她只是把手搭在我的肩头,桶里的水晃出很多,到家所剩无几,她弯腰把水倒入水缸,抬头的瞬间,我又看见她眼角的泪花,也许少不更事,不懂母亲内心所想,但我感受到母亲的坚强和伟大。从这天开始,我都陪伴她去挑水,雨雪交加时,我替她打着伞,听着她的教诲,这是我最刻骨铭心的感动,更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亲情,我们在那条路一直走到杏花飘飞。
清明那天,母亲突然被调走参加公社的“四清”工作,时间是一年。这是我人生中首次与母亲分离,母亲临走前,眼含着泪水,千叮咛、万嘱咐;
“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将煤炉通风口打开,不要中煤气”。
“挑水时,不要掉到老井里,摇辘辘要一鼓作气,否则会被辘辘摇把打断胳膊”。
“自己要学会做饭,拉平车去买煤买粮,请同学于凡兄弟帮忙,夜里走路要结伴而行,记着带手电筒和棍子,有狼可以防身等等”。
母亲的心很细致,告诉我替换的衣服在这里,粮本和粮票在那里,零花钱由李德超阿姨代管,再下来是母子抱头痛哭。母亲依依不舍的走了,那扇破木门关上的瞬间,隐藏在柴房角落的孤独和恐惧,瞬间就把我吞噬了,这更加深我对母亲的依赖和想念,残酷的现实,逼着我必须自食其力的活着。从此,去老井挑水变成想念母亲最美好的过程,井绳已成为连接母亲的缆索,辘辘也不觉得太沉,长长的井绳,一寸寸缠绕在辘桶,仿佛正拉近与母亲的距离,于是,更加奋力的摇着。
离开母亲的日子很难熬,买煤要拉着平车走20里地,道路崎岖坡陡,即便于凡兄弟帮助也难走,只好节约用煤,晚上把炉子封起来,但心里总怕封不好,或大风倒灌烟筒,就中煤气了。挑水也是心惊胆战,唯恐跌入老井,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愿,坚持下去,等母亲回来。也许是我的信念,也许是上天的眷顾,我居然活了下来,而且也没有得病,连感冒都没有。现在回忆起来,绝对是个传奇,应该是对母亲的想念转换为动力,支撑着我的信念。
又是一年杏花开,母亲终于回来了,她瘦了,还有了白发,团聚时的心情,用什么文字形容都显得苍白,唯有彼此抱头痛哭。母亲的归来,让原本凄凉的家重新温暖,母亲犹如一把伞,继续为我的人生道路遮风挡雨,母亲对我的影响,始终伴随着我成长。母亲还给我另外一个惊喜,托人在北京买的一本书,书名是《绿竹村风云》,这是我人生拥有的第一本书,让我爱不释手。从此,她每天都给我读书,挑水也带着它,把水打上来,一起坐在扁担上,当她读到:“插秧时的“牯牛相踢”,把我和母亲逗的哈哈大笑。这本书遗失很久了,告别那口老井也有四十九年了,母亲也不在世了,但这些记忆,永远留在我的心里了。 那口老井的水,犹如母亲爱的心泉,四季不涸,清冽甜润,它滋润着我、养育了我,我忘不了母亲眼角的泪、眼中的忧郁以及对我的期待,对母亲与那口老井的记忆,刻骨铭心,更像老井的水,滴滴甘甜。
征稿信息
清明时节“雪”纷纷,这个清明有点“特别”,但也不改往年的优雅与宁馨:它或承载了春意萌动的情思,“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或寄托了追远祭祖的哀情,“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当往年的新绿、微雨遇上风霜、雪霰,会在你的灵魂深处诞生怎样独特的生命体验呢?继承传统文化习俗,响应时代热切呼唤,清明时节,不一样的清明,由你来书写。具体征稿信息请点击此处。
人气奖评分规则
投稿作品将会在公众号“海淀区作家协会”进行展示,展示期间个人作品的人气评分将由 阅读量×0.5+点赞量×1 组成,最后人气排名前5位的作品获得人气奖.
排版/编辑:罗 晴
审核/主编:童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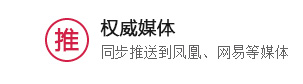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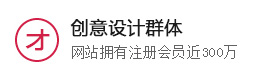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