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袁旭
学院:影视艺术学院
专业:广播电视编导
年级:2017级
我觉得文字或者文学,是最有穿透力的一种艺术,没有之一。当我们执着于笔尖时,就可以把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跃然纸上,那样的感觉,是一种如同一种隐秘的快乐。
我手写我心。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这条路很艰难,可青春的力量不就是来自于不满现实吗?
他个子在男生中不算高,这给了他运球的优势。
篮球在他手和地面间迅速的徘徊,他从球场中间跑到篮筐附近,不等对手反应,他又纵身一跃,下一秒,篮球已经从篮筐中垂直落下了……他和队友击了掌,拿起矿泉水仰头喝起。他大抵是知道我在看他的,仰了仰头,冲我做了个胜利的姿势,然后又摆摆手,示意我回去上课。
这是我初三,他初四时我们的交流方式,那时候,他们班的课表我记得比他清楚,每次他们班上体育课,我都谎称上厕所,跑出教室偷偷趴到窗户上看向操场。而他每次打球都会选择靠近教学楼的篮球场,是为了让我看的方便?大概是吧!
虽然谎称上厕所的时间就那么一两分钟,可只要看他一分钟,无论进球与否,我都高兴。
这个他,填满了我的整个青春。
他比我大一岁,初三开学时认识的。他们中考复习借书,借到了我这里。那是本初三上册的语文书,当时很犹豫借还是不借,后来听说他学习很好我才借的,学习好的人一定格外的爱惜课本。因为教材我们也在用的缘故,我们互相交换了课表,我和他每到各自语文课的时候,我都会奔波在三楼和四楼之间。
四楼本是学长学姐们的“地盘”,这本语文书让我和这层楼有了如同蓝天和白云般微妙的关系,白云在蓝天的映衬下,是那么的宁静、纯洁、轻盈、飘渺。
第一次正式借书前的夜晚,我的那本八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整齐的摆在书桌上,旁边是一张精美的包书纸和各种美工工具。我把包书纸小心翼翼的折在新书上,平时我习惯用牙齿咬断的透明胶带,也让我用美工刀整齐的剪下,那一刻,新书的墨水味闻起来竟有些淡淡的清香。包装好后,又挑了一个以前收藏的礼品袋再次外在包装。我搞得这么正式,不为别的,因为我爱惜书。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我的教室找我,他像做贼一样漏出半个脑袋,伸向教室,有同学知道他是学长,在我给他递书的那一刻,发出窃窃的笑声。笑声让我红了脸,没敢正视他的眼睛,“谢谢”二字从嘴里吐出之时,却看到了他漏出的一排整齐的牙齿。
前几次,我还不敢去学长学姐们的“地盘”上,都是他跑腿,久而久之,三楼和四楼也不过是几步的距离。有次我去他们教室拿书,竟和他教语文的班主任碰了个正头。
“喂,学哥,语文书!”他迷迷糊糊从桌子上起来,额头中间有一大片的粉红,他伸了个懒腰,拿起书从后门笑着像我走来,然后他们班里是一片呼声。
谁又能料到,那个教语文的老头又闻声赶回来呢,他班主任先看了看我,好像在思考这是哪班的学生,我困窘极了,他却一脸淡然,我拿书拔腿就跑,却还是听见了那个老头略带戏谑的呵斥。
是从撞见班主任那天开始吧,我的语文书上除了重点标记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彼此的小心思在课文的空白处得到释放,在那篇《关雎》的空白处,尤其的满。直到我初四复习再拿出那本书,才发现,已分不清诗句和注释的界限,却分得清他的字迹和我的字迹。
那本书归还之时,他已经过了学习之路的第一个小关卡——中考。他高分进入省属重点高中,给了我无限的奋斗力量,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八年级上册的语文书中那篇《关雎》是最好的精神慰藉。当我也顺利进入他的高中时,那般的喜悦与兴奋,大概就如同当时写《关雎》的诗人吧
一年又一年,我高一,他高二,我高二,他高三,我们对彼此学哥学妹的称呼未曾改变,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叫我,他说:习惯了。
大概我们的“早恋”比较低调,又是不同的年级,而他成绩又好,所以从来没有被通报过。
所有美好的幻想为枯燥备考的时光添了几分恣意,晚自习前食堂的某个角落、晚自习后从学校到家的那段马路……都充斥着甜蜜、苦涩、和成长路上的忧愁。
那一年七月份,他收到了华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二年七月份,我知道那些个无数躁动的青春的日日夜夜只能以记忆的方式再与我相遇。而那篇《关雎》是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细节。
保存记忆的方式有很多种,文字是我喜欢的。你看,就算我把初恋的记忆沉淀在心底只中,它也会偶尔跟随着跳动的心房深邃到我们的的血液,执着于我们的笔尖。
山有小口之时,仿佛若有光,心有小口之时,初恋便是唯一的光。
上一篇:【征文天地】陈雨欣 | 幸福花儿开满校园
下一篇:【征文】十年前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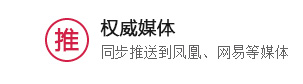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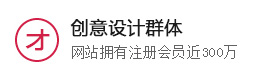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