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厚德杯”有奖征文大赛启事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
峡山文化
【“厚德杯”征文大赛初选作品】1067号
谢谢你来过我的世界/王小莲
小时候,生活简单,时光也慢。很多人、很多事在我的童年里出现。几十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我慢慢长大,它们也一一坠入岁月的湖底,在绵长的记忆深处散发出若隐若现的光芒。
1.炕
每次回老家,吃过饭,母亲都会拍拍她的炕头说:“快到炕上来歇歇,回来一次不是拖地就是抹桌子,也不嫌累得慌。”
有时,我会顺从地躺到母亲的炕上去.看着她日益稀疏的白发、不再清澈的眼神,听她絮絮地讲话,看她昏昏然睡去,与炕有关的画面一帧一帧浮现在面前。
很小的时候,村子里没有电灯,庄户人家的夜生活都拢在一盏昏黄的灯影里了。
那个时候,冬天的夜晚很深很长,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给拮据的生活增添一点收入,母亲会在暖暖的炕头上绣花。
她在炕上支一个绣花的架子,而我的被窝正好在窄窄的架子下面。每晚,我躺在那个绣花架下,透过稀疏的网眼,看一双灵巧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网格中舞动。
躺的太规矩,一会儿就累了。我伸伸腿,一不小心触到母亲的脚,她的脚不知什么时候伸进了我的被窝里,在里面藏着取暖,我用小小的脚趾在她的脚心里挖一下,她就用大脚趾回挠我一下。我悄悄调整一下姿势,伺机再次偷袭一下那双大脚板,母亲的声音便笑盈盈地传过来:“不要乱动,会打翻油灯哦。”
被识破计谋的我,会暂时收敛一下,矜持地躺在被窝里,看灯影里的飞针走线。一会儿,一朵花便开在了我脸庞的上方。
网格里那些精致的图案在我的脸上投下了影影绰绰的影子,而我不知什么时候已在影子里甜甜睡去。
冬天的太阳也跟我们一样,会赖被窝。但是,母亲却早早起床,去为我们做早饭了。一墙之隔的屋子外面,风箱一下一下有节奏地响着。灶台里燃烧着麦秸草、玉米秸或者棉花的木枝,发出轻微的噼噼啵啵声,熊熊猎猎的火焰在灶里欢腾奔涌,沿着固定的通道钻进了炕洞里,炕慢慢热起来。我有时会从被窝里伸出手,摸一摸粗粗拉拉的炕的墙皮,它热乎乎的,散发出一种燥燥的、淡淡的草木灰的味道。每天早上,当屋子里飘出粥香的时候,母亲便唤我们起床,而我总会缩进被窝假装听不见。
从小我就怕冷,母亲为此缝制了厚厚的棉裤和棉袄,我穿着它们,像一只笨笨的企鹅,摇摇晃晃走在上学的路上。即使如此,我的手脚依然觉得冰冷异常。
每到夜晚来临,我爬到母亲早已铺好的被窝里。炕,张开它宽厚而又温暖的怀抱,拥我入怀,用它一腔的温度和热忱慢慢消融我小小身体里的寒意。
在它的怀中,一整个冬天我因寒冷而蜷缩不敢伸展的身体慢慢舒展开来。
那时候,炕还是我心目中的大海。我会把所有的被子搬到炕的一角,把它们叠得方方正正,一床一床高高地摞起来,然后从上面往下跳,我要体验一下从孤岛跳入大海的感觉。跳进海里之后,我奋力挥舞手臂,踢蹬双脚,我变成了一条鱼儿,在海里尽情地游啊游。
炕,还是我心驰神往的草原。我经常把床单扯下来,用各种能够用的物件,在炕上撑起一个帐篷,那是我的“蒙古包”。我会在“蒙古包”里摆满自己的玩具,我在里面看小人书,在里面过家家,帐篷之外就是绵延无尽的草原。躲在“蒙古包”里,我仿佛能够听到草原上飞驰的马蹄声。
有时候,半夜里一道尖锐耀眼的闪电会突然刺破窗口的黑暗,轰隆隆的雷声在头顶滚过,接着就是声势浩大的雨,从遥远的地方排江倒海而来。躺在黑暗里的我,听着外面天翻地覆一般的雷雨声,我觉得,炕像极了一艘巨大而坚不可摧的轮船,乘坐这艘大船的我,是那样的安全。
后来,长到大一些的时候,我就不怎么喜欢炕了,因为我觉得它太“老土”,不如那些木制的床整洁而好看。
再后来,父母亲真的把炕给换掉了,我睡到了一张新的木床上。我的世界里每天都有新的东西不断涌入,炕也被我渐渐淡忘。
人到中年,我的父母双亲却老了,像孩童时的我一样,他们也开始畏寒怕冷了,哥在老家盖的房子里专门给他们盘了一个炕。
每次回家,摸着那个温软的炕,儿时我与炕耳鬓厮磨的那段时光便倏忽一下回到了面前。
2.草垛
在那些或近或远的记忆里,草垛也是儿时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
小时候,田里的小麦或玉米收割之后,大人们会把麦秸草或者玉米秸攒成一个个整饬而紧实的草垛。它们像一个个城堡坐落在庄户人家的场院、胡同或者道路旁。
放学后,我们把书包一甩,草垛就成了我们的赛场。
场院里那些挨挨挤挤的草垛中,最高的那个就是我们要征服的对象,谁最先爬上去,谁就是那个城堡的“王”。
一声令下,孩子们喊着“冲啊!冲啊!”像一群出栏的猪仔一样,兴奋无比地奔向草垛。
爬到那个最高的草垛上,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但那时的我们却懂得采用迂回战术,矮小的草垛是我们最先攻克的目标,爬上一个之后再跳到另一个上面去,连续爬了几个草垛之后,最高的那个“城堡”就在眼前了。
站在高高的草垛上,飘着炊烟袅袅的屋顶、高高的树杈上归巢的鸟儿、远处隐隐约约的村庄,一切尽收眼底。像打了胜仗一样,我们对着天空和远方呐喊。
黄昏硕大的夕阳鲜红鲜红的,“残阳如血”就是用来形容那样的一场落日吧,只是,那时的我们除了被那种美震撼得发愣,一个字也说出来。
西天像一个巨大的画布,一把看不见的刷子把绛紫、靛青、暗红、橙黄的色彩一笔一笔浓重地涂抹上去。慢慢的,各种颜色互相渗透交融,最后变成了单一的黑色。天空把夜的帷幕徐徐放下来,顺手在上面洒满了碎钻一样的星星。
如果说顺滑的麦秸攒成的草垛像城堡,那玉米秸攒起来的草垛就像一个倒扣过来的大沙漏。一日三餐的灶火把里面的草秸掏出了一个大大的洞,那个洞就是我们躲猫猫的地方。我们爬进洞里去,把外面的一层玉米秸往中间拢一拢,以便挡住洞口。躲在洞里的我们,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在周围忽近忽远,我们屏住呼吸,紧张地盯着洞口,像躲避前来扫荡的敌人。
忽然,身后小伙伴的一声大叫,触断了那根紧绷的弦,我们被他唬得跳起来。
一只小耗子,被我们冷不丁堵在洞里,上蹿下跳地想找一个出口逃命,慌不择路,撞到了大气不敢出一口的小伙伴身上。
结果,外面的“猫"毫不费力就逮到了已在洞里乱成一锅粥的“老鼠"们。
草垛,不仅是小孩子喜欢玩的一个地方,老母鸡也喜欢。
有一次放学回家,我路过胡同口的一个草垛,瞅着草垛的上方有一个凹陷,直觉告诉我那里一定藏着一个秘密。
我踮起脚尖,抻长了脖子,果然,两颗粉色的鸡蛋卧在软软的草窝里,安静而又亲蜜。
我兴奋极了,小心翼翼摸出来,用衣服兜住,内心呐喊着跑回了家。
当我洋洋得意地把意外收获交给母亲时,母亲面容平静地说:“怪不得隔壁的奶奶说她的芦花鸡不生蛋了呢,原来是跑去草垛做了一个窝。"
一脸蒙圈的我,看着母亲把鸡蛋给奶奶送回去。从那以后,我知道,即使是从草垛里捡来的东西也是不能要的。
草垛,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不会说话但无比忠实的玩伴。
我们在草垛旁跳过皮筋,靠在软乎乎草上晒过太阳,还头朝下双手着地,把腿打到草垛上,练过倒立。
草垛又像一个忠厚而沉默的慈祥老者,任我们在他膝下承欢,追逐嬉闹。
草垛,陪伴了我们整个的孩童时代。
3.露天电影
"今晚要放电影喽!"
"谁说的?"
"还用说,演电影那个地方早都摆上家伙了!"
"那得赶紧做饭去,吃了饭早去占个地方!"
小时候,如果听到这样的对话,村子里就真的要放电影了。
天还没黑,村子里东西南北四条街的交叉路口,也是村子里最宽敞的地方,已经热闹起来了。
放电影的工作人员已经早早把幕布撑了起来,幕布前的空地上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摆上了稀稀拉拉的马扎、板凳和小椅子,像棋牌上零零落落的棋子。
村里的一位爷爷,推着一笸箩还带着余温的炒花生和炒瓜子也到场了,每当村里放电影,他一定会如约而来。
一群小孩子,衣兜里揣着妈妈给的零钱,围在爷爷的笸箩前,递给他一毛钱就能换回满满一衣兜的瓜子或者花生,剥开一粒投进嘴里一嚼,满嘴的香。
那时,一兜瓜子与一场露天电影是绝配,就像现在的一场电影少不了一桶爆米花那样。
每当放一次电影,天空就好像吃了醋一般,迟迟不把它黑色的大幕落下来。
坐在场子里的人们却没有一丝抱怨与焦躁,仍心平气和地坐在幕布前,悠闲地嗑瓜子、抽烟、嗡嗡嘤嘤地说话,孩子们在场子里东颠西跑、追逐嬉闹。
瓜子的香味、香烟燃烧后的特殊味道,工作人员调试音响丝丝拉拉的声音,像一曲乐器丰富的合奏,在场子上空荡漾着。
电影终于开始播放,场子里也安静下来。
那时看过的很多电影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观后感却异常激荡人心。当那些恐怖的场景和诡异的背景音乐响起时,我看到胆小的孩子会捂住耳朵或者闭上眼睛,把头钻进大人的怀里。
投射到幕布上的那束光影里,不知是底下抽烟人吐出的烟雾,还是别的什么,像游魂一样的东西丝丝缕缕飘飘幽幽升到空中去,然后消失在黑黑的夜色里。
一场过于激烈和恐怖的电影看完之后,它直接粉碎了我的胆量。当人们提溜着马扎、板凳呜呜泱泱散去时,我会站在我家门前的那条胡同口,望着里面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处,迟迟迈不开脚步。
那时的电影,也让我确立起一条好人与坏人的判断标准:好人都剑眉星眼,正气凛然,侠骨柔肠;坏人都贼眉鼠目,形象猥琐,无恶不作。那种非黑即白的评判准则一直影响了我很长很长的时间。
再后来,我慢慢长大,才渐渐觉得,世间的善恶美丑,远没有那样简单。
一个人既可以善也可以恶,既可以美也可以丑。取决于善恶美丑的,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人性的开关。当人性中的善意开启时,人就变成一个柔软而有温度的好人,当恶意占据了人的内心,人就变成了一个冰冷而坚硬的坏人。
世间哪有完美无缺永远不变的天使,又哪有与生俱来万恶不赦的恶魔。
但是,电影中那些触动了灵魂的东西,是无论穿过多少岁月时光,也无法忘却的。
《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小花》里那个苦苦找寻哥哥的小花、《少林寺》中为父报仇、为民除害的小虎,甚至它们的原版主题曲。虽然它们披着厚厚的时光之锈穿越而来,但,当它们从纷纷扬扬层出不穷的时尚和流行元素中翻山越岭来到你的面前时,我相信,那份曾经的情谊,如雨后的种子,会瞬间刺破那层坚硬的土层,从你心里冒出芽儿来。
4.小表哥
小时候的我,时常被送往舅母家。少了一个尾巴一样在她身后纠缠的孩子,母亲便能够抽出一些时间来照顾田间地头的那些活计。
舅母家大一点的哥哥姐姐白天都有事做,年纪最小的表哥便成了我的专职看护。
小表哥大我几岁,性情极好,也极会玩。
舅母家村子不远处有一条小河,那次表哥牵了我的手去往河边。
表哥把我安置在河边一块结实牢靠的大石块上,自己则利落地下到河中去。
“在这儿好好的,等我回来。 ”
晃晃悠悠的河水没过表哥的腰身,只露出瘦瘦的肩膀和胸骨,他拉住我的手,确认我听懂他的话后,回过身去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里。
我一个人待在大石头上,看看四周,除了幽幽晃动的水面,一个人也没有,周围安静极了。那时的我并没有感到不安和恐惧,只是乖乖地蹲在那里,安静地盯着水面,我确信哥哥一定会回来。
不久,我看到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黑黑的脑袋一晃一晃地向河中心飘去,一转眼又不见了。
然后,挨挨挤挤的荷花丛里,一支大大的荷叶忽然动了一下。
在我还盯着水波出神的时候,一个黑脑袋呼啦一下从水里冒出来,是哥哥回来了!他像一只落水的小狗一样晃动着脑袋,细碎闪亮的水珠纷纷扬扬落进水里去。
表哥手里捧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叶包,荷叶的缝隙里露出白的、墨绿的、花的蛤蜊和螺。
表哥抹一把脸上的水珠,把荷叶包递到我手里:“拿好,中午给你做好吃的。"
那些螺和蛤蜊怎么做的,是什么味道,我早已不记得,只记得表哥把荷叶放到我手中的时候,周围的河水被表哥搅动起一圈圈的涟漪,在阳光里发出明晃晃的耀眼光芒。
夏天的玉米地,也是表哥经常去的地方。那里面生长着一种结了“焉柚儿果”的植物。表哥钻进玉米地里,去为我寻找那些酸酸甜甜的果子。回到家,他把半塑料袋的紫色果子洗干净,放到一个瓷碗里,再递给我一把小勺子:“快吃吧,可甜了!"
小小的紫色浆果,像被施了魔法的葡萄,一颗颗缩小,如我的小手指甲那般大,圆溜溜的,晶莹透亮。我挖起一勺子放进嘴里,它们争先恐后在我嘴里爆掉,比芝麻还小的果籽夹带着甜甜的汁水瞬间溢满唇齿。
表哥坐在我面前,看着我把一碗的“焉柚儿果"吃完,他哈哈大笑:“看看你的嘴,像不像一个大妖怪!”
我站在镜子面前,看到自己舌头、嘴角被焉柚果儿染成了紫色,还抹到了脸上鼻子上,我张大嘴,张牙舞爪地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觉得自己真得变成了一个妖怪。
表哥变着法儿哄我,期待我能在他家多呆几天,为母亲能够多余出一点时间来,去做家里那些没完没了的活计。
但那时,我还是一个比较依恋妈妈的孩子,在表哥家呆不了几天,就开始嚷嚷着要回家。表哥用尽了各种办法想留下我:他给我逮麻雀,给我做最爱吃的醋溜白菜,带我去不远处的一个地方看屠夫怎样把一头嗷嗷乱窜的猪宰掉。
但是,当吃完了好吃的,看过了好玩的,我还是嚷嚷着要回家。
“外甥狗,外甥狗,吃饱了就走。"舅母一面唠叨,一面又极其无奈,只得让表哥送我回家。
表哥骑着自行车,我坐在他的身后,沿着一条宽宽的路往家走。表哥一面骑车一面说:“你跟着我玩多好呀,就那么想家吗?"
我一面觉得羞愧,一面仍然想快点回家看到自己的妈妈,那种感觉让我说不出话来。我默不作声地看着车轮紧贴着路边的狗尾巴草飞速向前转动,路沿之下就是挺深的沟渠。那一刻,我觉得小表哥是那样高大。
表哥听不到我说话,就把手伸到身后车座的位置,他要确认一下我是否还坐在车子上面。
......
而今,舅母已离世多年,我亦离家十多年。每次回老家,匆匆忙忙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公婆,吃一顿饭,便又匆匆赶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日常和俗事纠缠,已很少有机会再与小表哥见面。
但无论生活多匆忙,总有一些间隙,让记忆像光一样打进来。
现在想来,那段儿时的时光,因了小表哥的陪伴,而倍显珍贵和温暖。
注:作品转发数和点击率作为评奖参考之一。大赛征文正在进行中,欢迎踊跃投稿。
峡山文化
一个会排版、
会设计的公众平台
等你/讲故事/给我听
编辑:刘培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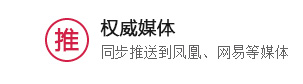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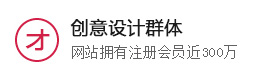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