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敏
大树,无论什么地方的大树,总能给人以惊奇和触动。可是,长在自家庭院里,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那些大树则总是更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即使离开了家到其他地方生活,也难免想起它们,想起与它们有关的已经烙在我们生命里的点点滴滴。
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树。但那些大树——更多的是因为或大或奇或者树龄的古老——甚至可能是一些有趣的典故,让我们记住了他们。比如,嵩阳书院的将军柏,阅世三千岁了,沧桑的树干又长出了许多新枝,让我们感受它的古老时又惊叹于它生命力的顽强;还有汉武帝错封将军柏的传说,也总能让我们这些小民百姓从皇帝的尴尬中获得一些乐趣。但这些穿越几千年的传说是别人的,我们不是里面演绎情节的人物。
打上我们生命痕迹的只能是那些我们从小就攀爬或者曾品尝美味果实的树,尤其是大树,这样的大树往往长在哺育我们长大的庭院里或大门前。我老家的老院里就曾有几株这样的大树。
我家的老院在大金店街东寨门内路南。在老家,我们有两处院子。老院是祖母传下来的遗产,我在那里生活了27年。院子是两家公有的,我家住在前面。老院的房屋低矮、拥挤,院落显得很狭窄。老院的特色就是里面长着几株大树——我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的欢乐与那几株树紧紧相连。
老院北面临街的小院子里长着一棵大泡桐树。树很粗很高,以至于粗得高得我那时不能攀缘上去的地步,而幼时的我在小伙伴们中间是以善于爬树著称的。因此,那时我每一次去小院子玩,那棵大泡桐树都让我敬畏,是呀,那样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怎样能长出那么粗那么高让我上不去的树呢!
可惜的是,这棵大泡桐树没有活到我长大时征服它。当然,它不是老到自然死亡了,它的砍伐是因为镇上的修路。镇上的老街长而窄,所以,干部们决定修直扩宽它。而我家临街的小院子有一半在新路范围之内,靠墙而长的那棵大泡桐树被强令砍伐掉。父母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卖给一户需要给老人准备棺材板的人家,虽然卖了600元钱——在1977年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我也因此失去了许多围绕着它的盼望和欢乐。
老院南屋的东北角长着一棵石榴树。那是一棵很老的石榴树,树干苍黑,有些地方已经空了,潮湿的天气甚至会长出一些菌类。树干向南倾侧,好象已老得不堪重负自己的身子。虽然这棵石榴树已经是老朽了,但每到春季,它照样抽枝吐芽,开出火红的石榴花。秋天时,红红的大石榴就成了我和妹妹弟弟的美味。这棵老石榴树也是我和伙伴们蹿房越脊的桥梁,它的倾侧的树干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然后就可上到我家的南屋屋脊,慢慢沿着就到了其他伙伴家的房上。不过,这样的事虽然刺激有趣,却也实在冒险,因此,我和伙伴们也经常为此受到家长的训斥甚至痛揍。
南北屋之间的通道上长着一株葡萄树。那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一株葡萄树,树径足有两把粗,而且通过十几米长的院子向东高高攀缘在我家的枣树枝头。这棵葡萄树给我和家人以及其他的邻里乡亲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每到夏天,葡萄架下的荫凉里总是坐满了和母亲关系比较好的街坊妇女:南院的海棠姑,西邻的花枝姑、恩芳婶子,东院的川妞姑,前街的莲芝姑、桂花姆姆、秋芬姆姆,崔家拐的何花老师,还有东西邻的两个奶奶。常言说:“两个妇女一台戏。”这么多的街坊妇女坐在葡萄架下,纳着鞋底子聊天,那热闹可想而知!葡萄成熟时,藤蔓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紫红色的葡萄,很是诱人。好客的母亲总要给来家里玩儿的街坊们摘一些尝尝鲜,没有吃到的还要派我或者妹妹送过去一些。
家里的那株葡萄树还给我和伙伴们留下神秘和浪漫。街坊的妇女们在聊天时说,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的日子,这一天要下雨,而且躲在人间的葡萄架下就能听到牛郎织女的说话,这很让我和小伙伴们好奇。说也奇怪,在我的印象里,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好象都要下雨,但是躲在葡萄架下能听到牛郎织女的说话,我们试了好多年都没有能实现。我记得曾问过母亲听不到牛郎织女说话的原因,母亲说:“你们太小,小孩子是听不到的,到谈对象了才能听到!”这很让我们失望,但也盼着自己长大,可惜的是,长大后却再也没有了儿时的那种兴致,当然我也明白了七夕节躲在人间的葡萄架下能听到牛郎织女说话的说法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从科学角度看是不可能的。
家里的那株葡萄树每年还给我家提供了一笔固定收入。每到葡萄成熟时,住在我上学的南岳庙附近的一个老头就要到我家里来买葡萄,老人是在学校门口摆小摊儿的。他用低于市场零售的价格把我家送人之余剩下的葡萄批发回去卖,这样每年这个时候,我家就有几十元钱的收入!
葡萄树最后也被砍掉了。砍掉葡萄树是我祖母的意思。按老年人的说法,葡萄树的阴凉容易吸引蛇,而蛇在农村是一种传说中能成妖成仙令人敬畏的动物。祖母怕蛇,后来竟然在一个夏天在葡萄架上真的发现了一条大蛇!于是,祖母下令把葡萄树砍掉,父母虽然心疼这株摇钱树,但还是顺从祖母的意愿把它砍掉了。
在院子东边的猪圈里,靠门长着一株大枣树。这株枣树有些奇怪:他的主干特别粗,却只有两三米高,之上的树干突然变细,高高的刺向天空。后来我读鲁迅的《秋夜》,读到“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处,就不觉想起我家的枣树,我就想:是不是所有的枣树都有一直刺天空的主干呢?后来知道不是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大枣之乡新郑,看到了田野间成片的枣树,那些枣树都被去了顶,短短的主干,向周围伸出许多枝杈,据说这样可以结更多的果,也便于打枣。
打枣,对于家有枣树的人家,是一件值得期盼的事。想一想,看着枣树发了呀,长了叶,开了花,结了果,又慢慢长大,变黄,变红,怎会不期盼着打下来品尝枣子们的甜蜜呢!所以,小时,每到秋季,我和妹妹弟弟包括邻家的孩子们都整天瞅着我家的枣子,想着打枣时怎样大快朵颐呢。打了枣,街坊邻居们都过了嘴瘾,好的留下来放好,腊八节时煮米粥放进去几个,腊月二十八蒸枣花馍时更是要用它唱主角呢!
不过,大枣树最后也伐了。父亲要在猪圈里垒兔子窝,枣树碍事,而养兔子当时是家里致富的大计,枣树就要让路。枣树伐了后,主干拉到木器厂解板,木匠师傅很不愿意接这个活,为啥?枣树木质太坚硬了,解板时太费锯条。当然,最后还是解了板,只不过多掏了些加工费。而解的枣木板,父亲把它做成了案板,替换了厨房了已用了十多年的不平的旧案板,继续为我家做贡献。
在猪圈的东北角则长着一棵大香椿树。有多大?粗的一人搂不住!这样粗的香椿树,很少见!村里人就认为它有灵异的功能。那一年,母亲和东院的奶奶在一块聊闲话,说道我的个子矮,总不如同龄的孩子长得高。东院的奶奶就告诉母亲,想长高,可以在大年三十晚上向大椿树祷告,很灵验的!于是,大年三十晚上,在椿树前摆上祭品焚香祭拜后,我就双手抱着我家的香椿树,按照东院奶奶教的歌谣念道:“椿树椿树你为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了好解板,我长高了娶新娘。”
树大,每年春天掰的香椿也就多!香椿叶腌菜,如同木兰头、甘菊芽一样,是我们这里取之草木的特色菜,很好吃的;香椿梗加盐煮熟撕咬着嫩皮吃,也很香的。掰下的香椿除了自家留一些,给在城里住的姑姑家送一些,其余的,母亲都送给了相处融洽的乡邻,这样,更多的人就能分享到我家香椿的美味了!
大椿树后来也采伐了。家里在过去东河的瓦窑沟批了新宅基地,上房盖好后,为了省钱,就让木匠把香椿树伐倒,主干解开制成了上屋正门的门板,这也算是物尽其材吧!
老院的这些大树为我们一家的生存力了大功劳!当然,这些大树作为老院的重要元素,也是我自小到大生活的重要场景,它们和老院的其它物件构成了我心中的老家的印象!现在,老院也不在了,我更是经常想起老院子那些大树,想起那时的生活,想起围绕大树发生的故事!
纷享登封
让中国感知登封的脚步
让世界倾听登封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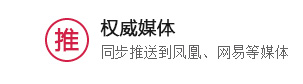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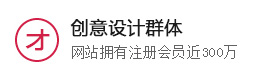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