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除夕夜,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宏森来到全国广播电视指挥调度大厅,现场坐镇指挥全国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和监测监管工作
2月16日是戊戌大年初一,宏森回家乡博山过春节。从媒体上看到毕玉奇先生呕心沥血进行音乐创作的故事,深为感动,表示一定要找时间看望一下毕玉奇。时间就定在春节当日,我说玉奇先生素称“博山好人”,名望甚隆,家里一定是宾客如织、门庭若市,坐不下来说句话,还是请他出来一叙,可以好好地拉拉呱。当晚,在宏森入住的天隆宾馆,大家共同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
一见面,毕玉奇先生向宏森伸出了双手,共同的家乡情怀、文化执著,使这两双滚烫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玉奇先生说,感谢宏森部长来看我,我能有机会当面向您汇报创作情况非常高兴。宏森忙请毕玉奇先生落座:“毕老师快请坐!我一直很关心你的身体和你的创作!借回来过年的机会咱们见见面,说说话!”
“我最初写《乡籁》的动机很单纯,如果不是把它变成音乐,就是一堆废纸,往墙角一扔,后来陆续又写了一些,感觉不立起来也挺可惜,过去我不愿意说,现在看不说还真是不行。”
“该说就得说,毕老师,”宏森说,“实际上毕老师是在创造一个励志的故事,一个有志者事竟成的故事。所谓‘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们自己可能意识不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对后一代,对70后,80后,90后的一代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把你的作品推出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品能够如期面世,对毕老师个人来说是个完美的记忆,更重要的是还是大家的事。我们写的每一个文字,写的每一首诗,作的每一个曲子,看起来是自家的,一旦形成的时候就应该属于大家的,社会的,大众的,就不再是自己的了。因为这个智慧,这个灵感,来自于天地授意,天地孕育,既然是天地给了咱灵感,就要把它们还给天地,这个天地包括芸芸众生,还回去就是众生,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王家卫拍了一部电影《一代宗师》,里边有三句话,叫见自我,见众生,见天地。王家卫属于中华民族的怪才,奇才,在世界范围之内很有特色。咱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得好的不多,走得最好的应该是李安、王家卫,世界通行,他把中国文化变成了见自我,见众生,见天地。你仔细想想他就是儒道文化的合一,他其中用了八个字,如果毕老师将来举办音乐会的话,这八个字对你非常合适,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个事情你只要有执着的信念,必然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延续这个精神。
“王家卫一个片子要拍四五年,也没有剧本,连拍加琢磨,边拍边琢磨,拍完了,我说你拍完了?王家卫说应该是拍完了。过了半年又开拍。他用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和毕老师非常吻合。里边还有一些辩证关系,比如‘结一个缘,点一盏灯’,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台词,赋予了武术、武师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看《一代宗师》,王家卫四月份将在北京担任北京电影节主席,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到时候培国和毕老师去一趟,拜访一下王家卫。所以毕老师咱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薪火相传,都不是为了咱们自己。
“我看毕老师的身体状态不错,一点事没有,现在医疗条件也好了,琴棋书画一上阵就啥事也没了。我小时候,八九岁十来岁的时候,大概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我那时候就觉得博山真有高手,娶媳妇在大门上贴对联,到现在有些对联我还解不了,比如说‘歌诗工部其三句,乐奏周南第一章’,这个对联在博山用的非常多,叠道,赵家后门,都在用。还有一副对联我在别的地方没看到,叫‘幸有香车迎淑女,愧无旨酒敬嘉宾’,很有文化,特讲究。”
“博山文化的积淀很厚,”毕玉奇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博山的民谣俚曲非常悦耳,互相传唱,的确叫人念念不忘,前一阵子有人找到我,说七几年我去征集民歌,我记得有个曲子,唱给你听听,是描述煤炭工人找媳妇的,叫《黑不溜秋》,唱了四句,歌词有点俗,但曲调太好听了,当晚上我就写了个唢呐独奏《喜事连连》。忽然博山的老文化人钱殷之先生的儿子钱斌找到我,说俺二叔从收破烂的地方拿来一个东西,旁人也没有用,留给你吧!是收集的博山老民歌,我说这是冥冥之中如有神助。”
“是,不是为了自家,是为了大众,咋见众生?就得说出来。”宏森讲,“你看培国也在干这个事,你也在干这个事,这就是传承,文化就需要传承。培国的文章里说,你写《逛河滩》,先给老岳母听,老岳母给你第一个把关,叫人非常感动,我听了一阵,就想起小时候河沿边的情景,很生动。文化传承是大事。大家说孙廷铨孙阁老,也不是说他的官多大,还是说他的学问,说他的人品,给博山留下《颜山杂记》,如果没有《颜山杂记》,大家可能不知道孙阁老。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西冶街》,是我的一条街,又不是我的一条街,是中国的一条街,一直在琢磨,等将来有了时间。”
“有个片子《无问西东》是写清华大学一百年的,基本上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写出来了。《至暗时刻》是写温斯顿·丘吉尔的,看得我整宿睡不着觉。丘吉尔穿着睡衣坐在床头上,表情呆滞,傻乎乎地,几乎抑郁了,他老婆一开门,领进来一个人,英国国王,国王来了!却是个怀疑论者,就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都有他很黑暗的时候,过不去了,英国到底反抗不反抗法西斯?是当第三帝国的傀儡,还是为自由理想而战,争论非常大。身边的人提醒说,到地铁里边听听。丘吉尔说,什么地铁,我都不知道地铁站在哪里,然后一场戏,丘吉尔自己进了地铁,那是首相啊,人们吃惊,你不是丘吉尔吗?他挨着问,你叫啥名字?我叫某某某,你干啥呢?我干啥,你叫啥名字?问一圈,这时电影就戏剧化了,某某我问你,你叫某某是吧?你觉得咱是应该打呢还是应该和?是投降呢还是反抗?所有的老百姓都说得打啊!必须得打!丘吉尔问了一圈,有了决定,带领英国走出了至暗时刻。《至暗时刻》既是历史剧又是人物传记,人物刻画得那么好,而且就是那么两三天的事,又有点像话剧,把英国的舞台剧和电影融合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请毕老师看电影,这些片子得看,《海边的曼彻斯特》,把人生那种困窘说到杠了,一个普通人的困窘,面对生活的无奈,又得强打精神应付生活,看完了也是睡不着,写了个啥事呢?主人公李·钱德勒本人浪荡不羁,不着家门,有一天晚上,好不容易着屋顶找了一帮弟兄们在家喝酒,散了伙以后他也喝醉了,把他们送回去,家里着火了,老婆孩子全死了,在这之前他是浪荡不羁,老婆孩子死了以后他忽然发现做故故了,就得离开这个地方,到别处隐姓埋名去生存,但是家里又出事了,哥哥死了,撇下一个侄子,十七,他得回来给他哥哥处理这些事啊,就回来了,和这个侄子,那个感情,那种人生的无奈,无奈着浪荡着还得教育侄子,你不能浪荡,你得好好干,路上又碰见他后妻,见了面没啥说,演员演得那个好,说哭不是,说笑也不是,说了半天箩里簸箕不知所云,一堆虚词,看完片子就觉得发生在美国的事就是发生在博山的事,人性的最深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写好了,就是普世的东西。
“还有三月份要上映的《三块广告牌》,美国的,也是奥斯卡的大热门,必须得看。我看完了以后就坐不住,也是直抵人性,看完了以后坐不住得在原地转一转。还有一部中国片子名字未定,不是很多人有白血病?白血病人吃的药是瑞士的,在中国很贵,病人要耗尽家财,但是印度有一种盗版药,正版三万块钱一瓶,盗版才五百块,有个人就受人拜托去印度走私,五百进来卖三千,才是正版的十分之一,一帮人就跟着赚,赚着赚着打走私就不让进了,还把他抓起来,在我被抓之前我先进一大批药,甚至赔上钱把药发给病人,结果抓他的时候,白血病人都带着口罩,满满十里长街。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说你再补一场,五年以后,党的十八大以后深化改革,该药被纳入医保,他出狱的时候,他小舅子把他接出来,说我出来还用干这个事不?说你不用干了,咋着呢?纳入医保了,加了这么一段。即歌颂了人与人之间的善心,又批判了奸商无良,还如实反映了深化改革的进程。
作品是立身之本,根本在作品,就像出本书一样,你像培国出本《连浆》,博山父老乡亲都很高兴,都抢着看,因为培国是好朋友,我对培国的要求是全国人民都看而不是光博山的读者看,刚才我们也谈了这本书的一些问题比如文体意识怎么样强化文体怎么样选择一些更好的立意,创作出更好的一些不光是博山也可能是苏州可能是成都的读者都能读到的一些东西,这还得靠作品本身,也得靠一个视野,你来创作《乡籁》也好《琉璃》也好《孝妇河》也好,无论写什么东西是立足于本土,但是更要放眼于本土之外,你不放眼于本土之外是不行的,所以我要写西冶街我就迟迟不敢写,为什么不敢写?这条街不是我的也不是博山的,你要是写出来它一定是属于中国的一条街,必须和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你要不上升到这个高度,写西冶街,博山老百姓看了都说好,观音堂来在哪景德东在哪这不是目的,但是它又是一个起点,只有立足于本土才能找到切入点,切入点本身却不是完成点,切入点和落脚点是两回事,写《乡籁》也好《琉璃》也好,我个人斗胆觉得必须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放在民族文化的大框架中,而不是就本土而本土,本土是切入点,落脚点是国家文化民族文化,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跟着张宇声老师最大的收获是读书,你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四书》也好《五经》也好,《五经》都不敢说,就说《四书》你反复看觉着还是看不完,就那么薄薄的几本书,看不完是因为二十岁有二十岁的看法四十岁有四十岁的看法五十岁有五十岁的看法,这叫博大精深。中国文化怎么样来通过地方文化更好地呈现,地方文化是呈现中国文化的一个角度,必须得放到这样一个视野里头,至于专业化程度因为我完全不懂音乐需要怎么配器需要怎么样的格局需要分什么样的段落什么样的层次这一些可能有些专业化的要求,还是要和专业化想接轨。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民乐自成一体,和西方音乐差别很大距离很大,西方音乐当中一些好的点子好的方式方法可以成为开启中国民乐的一些启发点,当然不是生硬地搬过来放到中国民乐当中去,接受它的启发,他这个东西这么走,咱就学他一种方法,但是要进行本土化移植,要了无痕迹,真是要了无痕迹,所以毕老师的精力要放到创作上,外头这些事必然分散你的创作精力。在中国的文艺界你说金子有没有可能被埋没?肯定有,遗珠之漏、遗珠之憾肯定有,但是是金子总能发光,你比如我手里写了一本好书,说我因为不认识出版社的人出不来,这种情况有没有?有,但是你的书是不是真好,如果真好一定会有识这本书的有识之士,一定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道之后受到助力,一定是这样子。
“昨天唱了一天的《春节序曲》,中国民乐当中非常典型的作品,《春节序曲》一定有个地方音乐的起源,来自广东汉乐还是哪里我不懂,但《春节序曲》一定是中国人民都能接受的,东西南北中,都觉得是我的旋律,最典型的是吕其明创作《红旗颂》,实际上也是充分吸收了西洋音乐的元素,然后和中国的民乐充分地结合,这是非常典型的,当然这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又传统又经典可能要有些现代化的东西,就像二十年以前出现的中国民族歌曲的《黄土高坡》一样,和信天游有了很大的区别,有信天游的影子,更有了摇滚,有了爵士,包括有了嬉皮,那时候还没有嘻哈的色彩,现在有了嘻哈,等等这些东西你发现《黄土高坡》和《东方红》的时代又像又不像,哪一点像,但又不像,和信天游就完全不一样了,和《走西口》啥的也完全不一样了,但它还是《黄土高坡》。
“我一直提出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主义应该有个现代化过程,必须走一个现代化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是不行的,包括永远的巴尔扎克永远的雨果永远的托尔斯泰,精神上是这样的,具体方式上必须创新。我在上学的时候读托尔斯泰是如痴如醉,但是很快有人就把他冲击了,《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然后博尔赫斯,这些人很快就把他冲击了,这些更好,反而现实主义上了一个层级,永远有一个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在世界艺术史上或者说文学史上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现代主义,两大支柱,甚至互相影响互相融合。
“张宇声老师也建议在你自己的音乐体会里加进社会性的东西,比如奋斗,挣扎,悲凉,写琉璃的话包括工人经过那种烈火灼烤的那种东西,最终还是人性的主题,音乐太抽象,但还是要诉诸理性,要人们理解,像《命运交响曲》,文艺史上、文艺理论史上永远强调的是一定要把地域性上升到社会性甚至是更广泛的社会性,另一个是音乐性向人性向心性的提升,音乐性,人性,心性,最高贵的是心性,人性阶段停留在比如说呼唤、挣扎、追求、疲惫、悲伤,是在人性的层面,心性层面比如站在王明阳的高度,都是必然性的,当这个作品一出来以后,光芒焕发,心性就出来了。刚刚张宇声老师在评论培国这本《连浆》时指出,千万不要停留在简单写实主义层面基本写实主义层面,任何东西变成文字都要经过了你的过滤,经过了你的大脑设计,你不是一个传声筒你也不是一个留声机,你不能是席勒式的,你必须是莎士比亚化的,就是具备高度的历史品格和美学人格。
“我们是通过培国的文字传达了解你的事迹,因为过去我们没接触交流过。通过这些文字当中至少读出两种东西,一种是人间烟火,你肯定就在其中,是工人,是农民,博山的市民,子弟,人间烟火,喜怒哀乐,人情差事全部都有,咱们都有相同的经历,这是读出的一层意思。但第二层意思对艺术创作来说是更重要的,人间烟火以外还要有仙风道骨,仙风道骨就是超凡脱俗,虽在俗世当中,身陷滚滚红尘但又超凡脱俗,创作离不开这个东西,有人间烟火但是必须要有仙风道骨。
“还有一个观点,艺术的专业境界一定通过专业的方法和技巧,但艺术的最高境界一定是消灭方法和技巧,一定是让方法和技巧消弭于无声,这一点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入境、化境、灵境。入境,你要没有技巧你就进入不了这个专业方法的门槛,但是真正的专业方法是没有方法的,是消灭方法的,就是把技巧和方法融于无形,这是最高境界,灵境是超越一切的,凌驾于一切方法,这三个境界缺一不可,还是习近平主席引用的王国维的三重境界。王国维之所以是国学大师就是提炼了人生三重境界,第一层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人间烟火。继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知道这个事就这样了,没事,人间烟火看穿了,但是,我终不悔,甘于憔悴,不拿当事,不拿当苦,这不就是第二种境界?第三种境界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仔细想想,就是入境、化境、灵境。因此,对于地域音乐的一些曲调传承的方法,敢破才能敢立,敢立就要敢破,破立形成一个辩证关系,你比如‘东嘎啦秧西嘎啦秧’这个曲调,千万不可沉溺在其中,它毕竟是一个民间俚曲,民间俚曲属于在民间音乐上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才容易流行,‘东嘎啦秧西嘎啦秧’这个曲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简单,它通俗,它上口,很好,很珍贵,但且不可沉溺其中,它可不是最高境界,就像写字,那个笔一旋得赶紧出去,必须得赶紧出去,要进入到一个更加通用的更大的场域,我完全是不懂音乐班门弄斧,是一点体会,包括写文章也是,要带着反思,博山长期的积累,形成了成熟的城镇文化、市井文化,在博山文化丰厚的土壤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好的的习气,过去说的小市民习气,小市民的劣根性比农民的劣根性还重,对于地域文化不能失掉原则,必须要有辨析,有扬弃,该扬的扬起来,比如毕老师写琉璃写小炉匠,匠和家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匠人和艺术家有很大的距离,博山的琉璃也好陶瓷也好出了很多艺术大师,并没有在全国深入人心,不是像其他地区的艺术大师一样形成了很大的气场,很大的粉丝量,没有。原因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自得其乐,一亩三分地,我这个刻瓷,我这个工艺就到这,少一笔不行多一笔不行,不敢破不敢立,我给培国发微信,我说对博山文化得有辨析有扬弃,不能只要形成一个生态就一定是珍贵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鲁迅先生一辈子就在与之作斗争,在战斗,才是大师,他没有无原则地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托举到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地位,博山文化也是这样,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闪光点,也有很多薄弱环节,要有态度,有写作立场,该埋没的就埋没,该歌颂的就歌颂,家国必须一体,最怕的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沉迷,把家是家国是国分开。读者也有不同的层级,博山人都是看热闹,培国写了西冶街,税务街,不能变成故事版的地方史志,当然也是一种意义,还有更大的意义,所以出下一本的时候我就说要把篇幅留给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人和事,有一些既无价值有无意义的不一定去写,必须有主观处理的机制。”
宏森对《连浆》的臧否,对毕玉奇先生的勉励,让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倏然而逝。早已过了子夜时分,考虑到毕玉奇先生的身体,宏森提议请他早一点回去休息:“初一见到毕玉奇老师,非常幸会。”
“我本人微不足道,”毕玉奇先生起身,“只是感觉博山题材的东西就是写不完,好东西太多,简单的一句吆喝声变成旋律也很美。很多老人跑到家里去,眼泪婆娑地:‘你这个玩意,你这个东西弄得我成宿谁不着!’就得把博山的好东西留下,不然就是博山的罪人。听了您的一席话,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比原来更清醒了,更理性了,我会记住您的嘱咐,挖掘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
宏森一直把毕玉奇先生送至电梯口,始亲切告别。
(写于2018年2月21日)
促蛰刘培国先生第六本散文《促蛰》现已面世
博山谁人书社有售可加下方微信购得签名版
上一篇:春晚这些年,能看的还是你大爷
下一篇:@所有人,信宜市朗诵演讲协会给您拜年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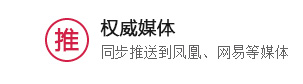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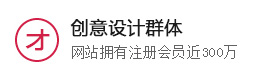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