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桃(沔阳)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由于长期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的童谣久唱不衰。在与大自然殊死搏斗的过程中,仙桃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近代藏书家卢木斋、卢慎之兄弟编辑出版了一套无比珍贵的《沔阳丛书》,将前人的诗词歌赋作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其中不乏经典之作。进入现代,“新闻巨子”羊枣和“金箭女神”杨刚兄妹又脱颖而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建国以后,仙桃也出过不少文学造诣很高的人才,可惜生不逢时,碰上反右和文革,半途而废,令人扼腕叹息。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跟全国一样,仙桃文学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三十年来,作家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无论面对的是阳光还是风雨,都勇往直前,让文学这朵奇葩在仙桃大地上越开越艳。
1、盘点舞台上的明星
仙桃文坛最鼎盛的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解除了禁忌,解放了思想,从而涌现出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他们接受了汉水的洗礼,吸收了千年古城的灵气,在当代文学的殿堂里一一亮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最早成名的是杨林尾人王振武。他是武汉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只有小学文化,1980年才开始创作。1981年,王振武以长阳茶山为背景,写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二篇短篇小说《最后一篓春茶》,一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于当时还没有“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一奖项无疑是最高奖项,意义等同于摘取了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他是我省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作家,为仙桃争了光。令人痛心的是,王振武于1986年患上脑溢血,半身瘫痪,三年后黯然离世。能将短暂的人生演绎得如此精彩,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是无憾的。
楚良是沙湖原种场合心村人,真名万良海。1981年,他以《蚂蚁和珊瑚》、《农妇和他的作家》两篇小说暂露头角,被文坛前辈评价为“文章好,人品也好”的好苗子。1983年,他的短篇小说《抢劫即将发生》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佳作频出,在全国兴起了楚良热,人称“北有邓刚,南有楚良”。在极短的时间内,他的中篇小说《玛丽娜一世》拍成了电视剧在全国热播,后来跟《合成人》一道,双双改编成电影。再后来,楚良离开仙桃,落户于西子湖畔,逐渐淡出文坛。
出生于仙桃镇的池莉后来居上,一跃而为当代文坛知名度最高的女作家,世人皆以收藏她的作品为荣。1982年,她的处女作《月儿好》一面市就引起轰动,被《小说选刊》转载,并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风行。1987年,她以一部《烦恼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誉为“新写实主义”流派的代表。1997年,她的短篇小说《心比身先老》又夺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迄今为止,池莉共获得“百花奖”等重要的文学奖项六十多个,《来来往往》、《太阳出世》、《生活秀》先后拍成电影,《不谈爱情》、《口红》、《水与火的缠绵》、《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有了快感你就喊》、《所以》等耳熟能详的小说有百篇之多,其中以仙桃为背景的文章不少,《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等等都是。
从芦苇丛中走出来的文浪也曾掀起过汹涌的文学浪潮。1990年,他以中篇小说《浮生独白》为标志登上中国文坛,被誉为中国当代“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之一。之后,相继发表《呼啸》、《孤独之狼》等系列中篇小说,凭借强劲的实力成为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并当上1995—1996年度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1996年4月,他的四部中篇小说《遥望》、《别梦依稀》、《杀人的垃圾》、《有一种欲望像飞》在《钟山》、《大家》、《作家》、《山花》四大名刊上同期刊载,时谓“联网四重奏”,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00年出版的李运抟著《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中对他有过专版评注。虽然随着文学的迅速边缘化,文浪沉思了十年之久,但梁艳萍刊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六期的《文化的缺失与新时期湖北作家及创作》一文还是肯定了他的重要地位。
在这些佼佼者的影响下,仙桃兴起了文学热。看到身边的人成功了,能写点东西的都跃跃欲试。有的仅仅是想圆童年的文学梦,有的则雄心勃勃,希望在中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当时的仙桃,到处都是诗社和文学沙龙。可能那个年代对作品的思想性强调得多一点,对文学性的要求远远比不上现在,因此很多人走进了误区,盲目地拥挤在这条狭长的通道里。
2、沉寂中的亮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钱至上、杯水主义成为主流。文学沦落了,成了金钱的奴隶。写作成了卑贱的职业。
仙桃文学进入了低潮。一度天真地以为,文学是一条康庄大道,到头来却发现此路不通。许多有天赋的作者在经历了忧虑和彷徨之后,带着对文学的失望和对财富的追求,一头闯进商海。1990年,刘诗伟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不忏悔》之后,忽然南下,以后再没有听到他涉足文坛的消息。像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面对渐渐没落的文学,他们潇洒地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文人下海其实是一种冒险,因为缺少必备的心理素质,很容易淹死。尽管当时淹死的不在少数,但回归文学的还是很少很少。
从事文学必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否则千万不要涉足。年轻人大多浮躁,很难坚守理想,老同志则不然,因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有过挫折和创伤,所以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痴心不改,只争朝夕,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坚力量。
李辅贵,以短篇小说《皮筲箕赴会记》在《长江文艺》刊载为标志正式走进文坛,在全国各级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先后出版小说集《蜜月》和长篇小说《小城G大调》。1990年,他的短篇小说《吻的荒唐》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引发热议,成为省内知名作家。
汪烈九,一位性格刚烈的文人,建国初期就在《沔阳文艺》当编辑,后来打成右派,经受了二十多年折磨。1979年,汪烈九获得平反,重操旧业。他老当益壮,一边工作一边撰稿,以文史资料为线索,写出了两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五十七年将军梦》、《王老虎传奇》、《偏安“副总统”陈诚》、《民国人物系列》等长篇小说和传记。198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纪实小说《怪将奇事录》,发行3万册。
还有两位老作家热衷于研究本地的人文历史,成果颇丰。一个是老《沔阳报》记者吴德才,先后出版了《新闻巨子羊枣》、《金箭女神杨刚》、《中山舰长李之龙》和《从牧童到博士》等九部长篇传记体小说。已故的市方志办干部傅献瑞,在有生之年写下了19万字的长篇传记《张难先传奇》,被奉为传世之宝。
值得一提的是,出生在通顺河畔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守华从小受到仙桃民间文化的熏陶,对民间文学兴趣浓厚,终生在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比较故事学》,后获得全国民间艺术最高奖“山花奖”。1999年,他耗时八年,推出了70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空白。在他的带动下,仙桃的民间文学创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以肖作玉、涂明炎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作家经常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故事作品,成为故事界的知名人士,至今稿约不断。
3、艰难的复苏
文学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集中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万万不可忽视。20世纪90年代,仙桃一跃而为湖北首强县市,并长期位列全国百强。经济腾飞了,文化却滞后了。本土作家涂阳斌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经济是城市的血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就像一个暴发户,迟早要垮掉。2002年3月,根据省作协的指示,仙桃市成立了作家协会,李辅贵同志担任主席。这个时期,大多数人的眼睛仍然盯在经济建设上,无暇顾及,作协实际上很少开展活动,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
从理论上讲,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要花代价的,就是需要一批无私奉献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一切都是空谈。
正在徘徊观望之际,一个契机出现了,《南方周末》的鄢烈山给仙桃人民带来了惊喜。鄢烈山,陈场人,时评专栏作家,著名杂文家。2005年,他的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一花独放不是春,如何把“一个人的经典”化成万紫千红的春色呢?不甘寂寞的仙桃人行动起来了。2005年春天,由市文化局退休干部胡铁树同志倡议,汪烈九、黄团员、田累、曾长坤、李宏银等同志相聚五湖外滩,在诗情画意中共商大计。6月16日,仙桃市“桃苑文学研究会”在天马大酒店正式成立,会长李宏银。这个文学团体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成为新世纪仙桃文学的先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一套仙桃人自己的书。
2006年3月,《仙桃文学丛书(第一辑)》由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向仙桃市建市二十周年隆重献礼。省作协副主席韦启文、叶梅为丛书题词,华师中文系刘守华教授作序,著名作家碧野、董宏猷为其中的两本书题写书名。这套丛书一共八本,分别为胡铁树、李洪源编著的《仙桃神韵》,曾长坤主编的《仙桃(沔阳)历代诗选》,李宏银的散文集《浪漫仙桃》,余克金的文集《心灵的颤音》,罗国亮的诗集《自吟曲》,段奇春的诗集《心声集》,王永华、肖仁沛、严晋的报告文学集《寻找远方》,以及田累的通讯特写《结束就是开始》。这套作品开了仙桃文坛的先河,令人眼前一亮。
2006年7月,仙桃市作家协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主席团成员由10人组成:主席1人,副主席8人,秘书长1人。另外还配备有副秘书长4人,聘任名誉主席4人。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意味着仙桃的文学事业迈开了新的步伐。
4、沉甸甸的收获
台搭起来了,戏可不能演砸。要团结会员,增强凝聚力,就必须建立一个平台。2007年元月,经市委宣传部批准,市文化局、市文联周密筹划,仙桃作协隆重推出了大型文学季刊《汉水文苑》。《汉水文苑》立足仙桃,面向全国,挖掘本地资源,联络名家大家,刊登了一大批好作品甚至精品,让人耳目一新。虽说是地方性的小刊物,但拿它跟市面上的任何刊物相比,都毫不逊色。从排版到印刷到装帧都非常精美,再看作品的质量,可以说篇篇精彩,令人爱不释手。这是仙桃有史以来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刊物,值得浓墨重彩。
《汉水文苑》定位成纯文学杂志,从头到尾都是一种冒险,但仙桃人坚持下来了。最困难的时候,湖北侨光石化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文昌格先生及时施以援手,每年捐助四万元,挽救了这项零回报的事业。到目前为止,这份杂志生存了将近四年,成为本地作家和业余爱好者的“后花园”。梁世楷、王仁波等老作家经常用它回忆往事,许立莹、雷俊波这样的年轻人则借此展露才华。省内国内的知名作家也十分关注,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如方方的中篇小说《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程远斌的随笔《陈友谅历史功绩初探》,熊召政的美文《对汉水的期待》,都在《汉水文苑》首发。在外仙桃籍作家池莉、楚良、鄢烈山、刘洪波、刘庆林、罗时汉、马世永,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吕志青、王芸、苏瓷瓷、郭海燕等等也应约奉献了上乘佳作。
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一切都应运而生,仙桃涌现了一股出书的热潮。如梁和平的诗集《蝴蝶》、歌词集《阳光频道》,吕永泽的报告文学集《蓝色瑰梦》,李培刚的长篇小说《命运回归线》,刘秋生的公安文学《真相的背后》和报告文学集《江汉儿女》,梁大新的个人文集《杏坛耕耘录》,达度的小说集《就这样把你征服》以及与妻子洛沙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体操神话》,还有王永华、小草的诗集,熊泽民、王仁波、程志峰、严启应的散文集等等,总数在四十部以上。作家们通过各种途径,把自己的心血结晶一一展示在世人面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008年初,市文化局局长胡晓华和市文联驻会副主席梁和平结合仙桃实际,根据作者的意愿,策划了一套《仙桃作家丛书》,由《汉水文苑》杂志社陆续出版。这种民间出书模式借鉴了一百多年前卢氏兄弟出版《沔阳丛书》的做法,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更是一次创新。这套丛书聚集了仙桃本土最活跃的作家及其作品,迄今已出版六本:李辅贵的小说集《撩开死神的面纱》,郑局廷的小说集《阳光总在风雨后》,李清亮的小说集《珊瑚》,张泽新的报告文学《汶川大地震》,猫郎的人物随笔《大话沔阳人》,胡铁树、傅长春合编的民俗文学《趣说沔阳话》。由于物美价廉,方便快捷,而且原汁原味,很快为仙桃籍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所接受,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加入这个队伍,渴望在仙桃文学史上流芳千古。
5、期待爆发
文学也有一个完成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仙桃人挺过来了。这几年,他们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收获不小,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长江文艺》、《读者》、《中国故事》等五十多家刊物发表文学作品上万件。
梁和平在歌词创作上独树一帜,他跟印青等著名作曲家合作,创作歌曲四千多首,获奖六百余项,成为享誉全国的词作家。其作词歌曲有五十余首被拍成音乐电视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有八首作品分获重庆、河北、江苏、湖北等省市的“五个一”工程奖,多件作品入选全国音乐学院的教材。在200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他作词的歌曲《和谐大家园》在零点唱响。在他的带动下,仙桃形成了一个歌词创作群体,佳绩频传。女作者陈琼瑶就是其中的典型,她创作的歌词《美丽的诸暨让美丽集合》在“美丽的西施、美丽的诸暨”全国歌词征集活动中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奖金丰厚。
郑局廷工作之余,醉心于小说创作。2007年,他的中篇小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在《长江文艺》发表后,很快被《中篇小说选刊》选用。2008年,又一部中篇小说《第三只眼》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与争鸣》随后头条刊载,评价非常之高。随后,他的《阳光笑脸》被《大家》刊载,《弯道超越》被《小说月报》收录。大约四年时间,他创作了二十多部中篇小说,其中的《预约爆炸》获得第三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堪称高产作家、丰产作家。
陈雄原是网络写手,他在天涯社区人气很高,被出版商盯上了,成为跨越网络和传统的两栖作家,五年出了五本畅销书:《麻辣典故》、《闲侃中国文人》、《公然走私的爱情》、《最红颜》、《历代才子才女的生活碎影》。陈雄是一个目光敏锐的年轻作家,他紧跟潮流,善于寻找热点、焦点,加上文笔犀利睿智、幽默活泼,每一部作品都深受读者喜爱。有人认为,文学是纯洁娇贵的东西,一旦走向市场,就意味着走向死亡。他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这种观点,充分说明文学之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宽。
陈雄的成功给网络写手带来很大的启发,大大增强了后来者的信心,网络写手不断涌现,为仙桃文学的发展储备了不少人才。包括出版了长篇玄幻小说《兵血不冷》的林丹在内,很多还不明身份的网络写手在悄悄成长。肖雅芳、蔚兰、猫郎等也从网络文学转战到传统文学,在《长江文艺》、《大武汉》、《湖北作家》、《打工文学》、《幸福》、《知音》等刊物发表作品。虽然暂时还没有出现顶尖的人才,但只要这种氛围这种势头能保持下去,总会有爆发的一天。
三十年不过弹指一挥,仙桃作协却走过了一段不平常的历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仙桃人勇于探索,开创出不同的道路,让文学的圣火延续下来,长盛不衰。
《文学仙桃》编写组
2010年8月
来源:仙桃社区
编辑:张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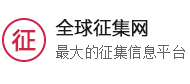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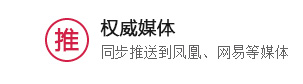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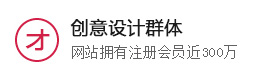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