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二丫坐上花轿的时候,便知道那都是一些注定要破碎的虚妄的梦。
在朦胧的泪光中二丫见到自己的舅舅。一袭旧旧白长衫的舅舅总是面带微笑,尤其在见到二丫的时候。二丫一生都忘不了舅舅对自己的呵护和栽培。只是,身为塾师的舅舅去栽培一个身为女子的乡村女孩二丫,无论怎么看,都显得荒唐和没有意义。但二丫的舅舅却不这样看。他常常颤抖着短少而白的胡须说,总会派上用场的,总会派上用场的,谁知道世道怎么变呢。多读点书,终归是好事,管他男孩女孩呢。二丫却觉得,舅舅对自己的悉心教诲,就好像是在无数凄冷的秋夜,去打捞水中月亮的影,不过是在做着一件美丽忧伤的事,结局是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不断重复的虚无劳作,舅舅做的这件便是最好的证明。舅舅死时二丫哭的最伤心。二丫知道,舅舅是她生命里一道微弱但是恒久的光。现在舅舅走了,人生的光,亦随之陨灭。如果没有舅舅,二丫读不成书。二丫的兄弟们,在他们七岁左右的时候,都被陆续送到舅舅的私塾里去。二丫的父亲没有野心,他不过是因着亲戚关系的方便,把儿子们送到私塾里去胡乱读几年书,粗粗识几个字,会算点简单账目,买卖东西不致上当受骗就罢了。那次二丫去舅舅家做客,和表姐妹们在后园玩耍,后来又跑去舅舅的私塾偷听,结果被舅舅发现了。当时舅舅正在检查学生们背诵孟子的《规矩方圆之至也》章。没有一个能完整背下来的。一个个背书都像小孩子拉大锯似的,半天“扔”一下。二丫掩嘴而笑。二丫的一个表姐,竟“扑哧”笑出声来。当然被舅舅听到了。舅舅把竹帘一掀,向外大声道,你们几个毛丫头,还敢笑别人,你们谁会背?几个胆大的表兄弟也在后面附和道,就是就是,你们背!表姐一撅嘴一扬脖辫子一甩身子往后一扭道,您又没教我们,他们教了都不会背,何况我们?舅舅却不生气,微笑着把头转向二丫道,你呢?我会。二丫低下头轻轻答道。当二丫诵至“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所有人都惊讶了,尤其是舅舅。二丫自己解释道,我听着哥哥们在家里背,就不觉记住了。舅舅惊讶之余复又问道,意思你懂吗?问完了又后悔。但是二丫又轻轻答道,懂一点点,大约是说先王之道仁而已矣的意思吧。这次的私塾偷听事件,让舅舅对二丫的聪慧惊叹不已。不久,二丫也进了舅舅的私塾,条件是不要束脩,白带一个学生。要不行就算了,她舅?二丫父亲直截了当道,我还指望她在家纺纱织布带弟妹呢。当然是答应了。舅舅死在雍正十年。那年二丫十三岁。舅舅过世后,由父亲做主,二丫与一秦姓农家子定亲。男子也识字,只是寥寥。勉强看懂时宪书,知道月份大小节气时日,仅此而已。是二丫一个远房姑姑的儿子。大二丫三岁。亲上加亲,不容二丫不同意。两人明显的不般配。二丫知道自己明珠投暗。但是二丫的出身和她女子的身份,都让她不可能还指望得到别的什么。五年后二丫出嫁。贰
辍学归来,二丫每日的工作不过是纺纱织布以及照料一个四五岁大的弟弟。二丫的母亲是一位终年面色苍白的瘦小妇人。常常头晕。她自己说,大约是生孩子太多落下了病根。然而依旧是生不完的生,苦不尽的苦。就好比是身陷泥潭的人,扒拉着双手拼命挣扎着要往上爬,却反扒拉下更多的石块土砾,再上不来了。二丫的母亲好比是生孩子的机器;又好比是二丫织的布,织的再多,不过是偿赋税、抵田租,又有哪一块做成了衣服温暖了自己的身体呢?
二丫有时想,这世上的人,谁不在生孩子?女人生下真正的孩子苦自己;男人呢,也生下孩子,叫生存。只要活着,谁不痛苦呢?生命不息,苦痛不止。二丫纺纱织布的时候,还得留神照看弟弟,几个年长的兄弟都跟着父亲外出劳作去了。母亲常常是大半日大半日的不停洗衣服。洗不完的洗,每天都累得她直不起腰来。二丫教他念唐诗。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二丫念一句,他跟一句。待背得熟了,又讲意思。甫一讲完,他便指着正手执梭子足踏脚板的二丫说,就像姐姐这样。二丫就笑了。顺手拿起木梭在他额前轻轻磕一下,道,你倒会现学现用。极偶尔,也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二丫喜欢写字。又顺带教弟弟认字。二丫的字,永远是那么端正娟秀。她曾在一片桂叶上写下全篇260字的心经全文,让生前的舅舅大为赞赏。这片写有心经的桂叶,二丫一直珍藏在身边。每当想念舅舅时,便把它拿出来,反复摩挲干枯茎叶上的端秀字体,轻轻念诵。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常常是,读着读着二丫就不觉泪水纷纷披了一脸。舅舅死后,二丫再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二丫因此学会了长时间的独处与静默。从前二丫说,我一听到琅琅书声,心里便有无限欢喜。当我手握书卷,就像饥饿的贫苦人手握双箸面对丰盛的菜肴。现在她再不说这样的话了。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那日二丫照例是在纺纱。一面又教弟弟读诗。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然后他来了。
后来二丫想,原来自己的一生,注定要以美人的身份去等待一场又一场虚空,直到荼蘼花落,直到生命的尽头。
二丫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乾隆元年的春天。那年她十七岁了。那天阳光灿烂、风轻云白、鸟语花香、蜂围蝶绕。
二丫看到他的脸。那是春日和煦阳光下四月的远山。漫山遍野野花盛开。满眼新翠松柏。成群白鹤在其间起起落落,那是他灿烂的笑。那天他穿一身洁白的孝服。身材修长。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
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个微胖的小厮。十一二岁。一双机灵的眼,冷不防便盯着人鹘落落转。还有一位和他年岁相仿的男子。同样是一身孝服,一张俊美的脸。却过分的白和单弱。不像个男子了。二丫不喜欢。二丫同样不喜欢的,还有那个满头珠翠的女子。人倒也长得好看,只是那一双眼,不经意间淡淡瞥过来,便让人感到森森凉意阴阴鬼意阵阵透人心寒。
他步入织布房。不过是简陋的茅屋。二丫的织布机就放在门左侧的南墙边。因为长年摩挲,光滑的木梭在昏暗的角落悠悠散发出幽寂的光。静静悬立的踏板是等待的姿势。纺车放在北墙边。墙角堆放满各式农活用具。平时都是随处乱放的。因刚刚得知有一位贵妇要来更衣,才匆忙收拾归置好的。所有农具都显露出仓促拥挤和窘迫的神情。
他是典型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富家公子,却有不耻下问的精神。看到锹、镢、锄、犁、耙,他无限惊奇,弯腰蹲身去长久观察抚摸它们。二丫感觉他的抚摸里有无限疼惜、喜爱和温暖。他又细心向身旁小厮一一询问它们的名称用途和使用方式。又随手拿起离他最近的一把毛竹锄头,在小厮的示范指导下略略弯腰做出下地锄草的样子来。
末了他点头感叹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诚哉斯言。种田人真不容易啊。原来我们府里每日吃的红稻米粥竟是这样一犁一锹一锄辛苦种出来的。他站起身的时候,二丫隐约看到他清秀眸子里潮湿的泪光。
伴他一同来的那白净男子,对这一切却毫不在意,亦无兴趣。蓦地一回首,倒发现原先被他们自打一进门便一直忽略的放在门右侧的纺车来。他亦俯身惊叹,又偏着头询问小厮它的名称用途和使用方法,又小心翼翼握住纺车的铁制手柄,轻轻摇转起来。满脸是惊奇的笑。那白净男子见状,也要纺着玩儿。他站起身来,让他。
不知怎的,二丫忽然生气了。她不愿那男子碰她的纺车。一下也不行。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她大着胆子一步跨进门来,一面又大声说道,你们哪里会弄这个,站开了,我纺与你瞧。天知道二丫当时心里有多慌乱。她长这么大,从没有和陌生男子这样说过话。而况还是这样两个和她年岁相仿的俊美男子。她只觉胸口兔鹿乱撞。好容易握住手柄,手才没有再抖。她轻轻摇转起纺车来。纺车微微颤抖着,在四月的乡村,仿佛是在唱着一首羞涩爱恋又缠绵的子夜吴歌。
他略略俯身靠近她,细细察看,默默叹赏。二丫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那白净男子在他耳畔悄悄说了一句什么,尔后又轻佻地笑了起来。二丫当然没有听清说的什么。而他, 却咬牙回脸骂了他一句。二丫便知不是什么好话,对那白净男子的厌恶又不觉深了一层。就想到抽身便走。正这时,就听到母亲在门外轻轻唤道,二丫头,快过来。
他走的时候,二丫细细数了他们一行的车子和人马,又不觉看了又看。二丫看到他和那个她所不喜欢的满头珠翠的女子同坐进了一辆马车,对那女子的厌恶亦不觉深了一层。紧随他们马车后面的那白净男子倒骑在一匹白色的马上。二丫没来由便想,应该是他骑在马上的,应该是他。而他的马,却被那小厮牵着,慢悠悠跟在车后,虚着鞍鞯。
空落落的马背,让二丫的心也跟着空落落的,只管云飞雾绕般惆怅。再看不到他俊美的脸,更不要说跨马而上时他一定会有的矫健身影。二丫被自己的胡思乱想吓了一跳,直到她怀中的弟弟一个扑腾,才让她如梦初醒。她猛地咬牙一转身,抱着弟弟独自默默走上回家的路。
父母笑逐颜开。二丫看不上他们粗俗的样子,所以那女人给赏钱的时候她没有去。不过他们笑嘻嘻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倒让她知道了这一群人是去一个叫铁槛寺的地方寄放一个早夭女子的灵柩。
肆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二丫第二日下午便一个人偷偷跑去了铁槛寺。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怎么敢?她怎么能?她就毫无顾忌?然而终究是去了。借着打猪草为名。途中她问了两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又问了一个老婆婆。她自己解释道,我姑姑家在铁槛寺旁边的村,我忘了路了。断断续续说了三次。说的自己满脸潮红。而实际上,那两个女孩只顾忙着玩她们的交线之戏,对于她的解释全然未听。老婆婆则有些耳聋,二丫的话好半天她才听懂了个大概。
铁槛寺不过是个普通寺庙。一般是明黄色高大铁门,上有匾额,题着寺名。大铁门两边照例一副对联,许是年深日久,字迹已有剥落。道是,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暮春的暖阳晒得人浑身发软。晒得人嘴里像含了蜜,心里像浸了酒,身子却早融化在满溢玫瑰花香的一池春水里。二丫把竹篮放在一旁,自己且软软坐在路边的一棵香椿树下。小小竹篮里盛满青草。竹叶草已开出星星点点明蓝的花,像女孩娇羞的眼。野牵牛细长的藤叶间已密密生出小小的淡绿蓓蕾。蚕丝草则真嫩绿的有如春蚕新吐出的长长的丝,仿佛悠长缠绵的思恋,吐不完的吐,思不尽的思。二丫不觉走至铁槛寺门前。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该进去。找谁呢?二丫不知道。她举起手,打算推门而入,又不敢。三次颤抖的举起手,又三次抖颤着放下来。胸口突突乱跳。双颊绯红。下午的铁槛寺异常的静。只余绵远悠长的诵经声低低送至人的耳畔来。像霏微缭绕的江南烟雨。二丫知道,这是寺内僧人做晚课的时间。侧耳谛听,诵的是阿弥陀经,不觉细细听去。听着听着人的心倒渐渐安宁下来,二丫不禁低声和着寺内诵经声轻轻念道: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
良久又听念回向偈道,
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皆发菩提心。
二丫闻听到此,不禁簌簌落下泪来。忽又听到寺内纷乱杂杳的脚步声离山门越来越近。晚课结束了。二丫慌忙拭去满脸泪水,匆匆离开。她终究没有胆量去问。她觉得自己难以启齿。实际上二丫此行最大的目的不过是,能与他不期而遇。她想望,自己来至铁槛寺,正迎头遇见他从寺内白衣翩翩,倏然而出,然后和他四目相对。哪怕只是擦肩而过一刹那,他长长的洁白衣角从她身旁轻拂而过,她也满足了。二丫这样想的时候,仿佛果真看到他正从寺内分花拂柳翩然而至,不觉齐耳红彻,一回身便弯腰提篮匆匆往回赶。一下头也不敢回。恍惚听闻寺内山门吱呀开启的声响,又听到身后足音春潮带雨般涌来,二丫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双眼灼热的睁不开。她跌跌撞撞小跑了一段路,侧耳谛听身后再无人声时,方才大着胆子匆忙而羞怯地回了一下头。日暮时分悠长曲折的寺前山路,除了她孤单的人,便是她孑立的影。朝前看,没有人;往后看,也没有。二丫的心空落落的就像被倒空了水的绿玉斗杯子,又像是口渴太久的人面对空空的杯子。二丫不知道该拿什么去充满这生命的杯子,这空空如也的绿玉斗。伍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二丫不知道的是,他早已不在铁槛寺。昨夜就去了水月庵。二丫还在这里痴痴的寻找和等待。她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又一个失望。她不知道自己的徒劳。她更不知道人生的徒劳。她在寻求生命的丰盈和充满,就像洒满月光或者缀满星辰的夜空。她不知道那其实是一场更大的虚空。如此盛大美丽,又如此虚空。亘古如斯。
二丫碰到一个小沙弥。十一二岁的年纪。正用两个木桶去河里挑水。二丫看到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兄弟们。不觉胆子壮了,脸也不红了,说话也流利了。二丫从他口中得知,他去了水月庵。离铁槛寺不远。接下来的路程二丫就不觉得自己是在走了。也不是跑。而是轻盈的飘飞到了水月庵。像风中的一片云、一瓣花、一缕烟。半个缺月挂在西天,幽幽照着水月庵。夜风的轻拂似是鬼的吟哦。二丫忽然有些怕。也找不到人打听。不知怎的,恍恍惚惚便来到一个亮着灯火的窗口。二丫不觉偷眼往里看,就像在织布房里偷看他。二丫看到那个她所嫌厌的女子,又看到一个满脸堆满恶毒谄笑的世故圆滑的老尼。又听那女子道,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二丫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再不敢听下去。又恍惚来到第二个亮着灯火的窗口。二丫看到他。然后又看到那个她所不喜的白净男子。二丫看到他拉着那男子的手道,你可还和我强?那男子温言软语道,你只别嚷得众人都知道,你要怎样我都依你。他方笑道,这一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儿睡下,再细细的算账。二丫不知道他们要算什么账,听得一头雾水。待要舒手敲窗,碍于有那男子在场,心下不敢也不愿。然而右足却像管不住似的早不自禁往前一迈,身子往前一倾,兜脸却早被一面蛛网密密网住了,二丫忙用手去抹,又黏了一手一脸油腻的丝。混合夜露或是雨水的蛛丝,是这样腻滞的缠绵。扯不断,理还乱。二丫觉出了脏。好容易抹净蛛丝,再定睛一看,眼前哪里有那一双男子的影?但见他独伴孤灯,正握笔凝神在一张纸上书写。二丫正准备大着胆子推门而入径言道,没成想公子也和我一样有静夜写字的癖好。哪知忽然一阵风来,把灯下纸笺吹落一地。再定睛一看,哪里有他的影?分明是窗前一盏孤灯,伴着窗外痴立的自己和委地寂寞的影。二丫就着灯光,拾起飘落到她脚踝边的那张纸笺,只见上面写道;那女子丢下纺车,一径去了。我只觉怅然无趣。一时上了车,出来走不多远,只见迎面那女子怀里抱着她的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说笑而来。我顿时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从此茅屋数间,男耕女织,料是众人断不肯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争奈车轻马快,一时展眼无踪。二丫撇下纸笺,双手颤抖而滚烫。摸摸双颊,也是滚烫。心扑扑乱跳。双眼又是灼热迷醉的睁不开。二丫闭上眼,同样滚烫的眼皮热热包裹着眼珠。无一处不是滚烫和颤抖。忽又想到这纸笺若是教外人见到,那可怎了?又忙忙睁开眼,低头遍地找寻,哪里还有纸笺的影?二丫就慌了。再抬眼一看,哪里是在水月庵,分明是在自己的家里,是在自己的闺房,是自己独坐孤灯,正握笔书写。可是那墨迹未干的纸呢?桌上没有。地下没有。墙角没有。门后没有。床下没有。寻遍房中每个角落,毫无踪影。二丫慌得手脚乱颤,急如雨中蝴蝶。正这时,忽又听到有人大声敲门,像是自己的父母,又像是自己的兄弟,又像是那白净男子,更像是他。敲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越来越疾。二丫万急齐聚,不觉呀地哭出声来。这一哭,倒醒了。但见自己好端端躺在自家床上。只是身儿滚烫,头晕目眩,全身乏力。卧室门外,能清楚听到父母正一递一声说着话:这孩子,许是打猪草累着了,回来一句话不说就躺床上了,晚饭也不吃。管她呢。也没见打了多少猪草,哪里就累着了?陆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二丫后来就变得爱去织布房了。以前也每日要去,但那只是单纯为着纺纱织布;现在去,则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二丫去的时候,总爱先在窗口漠漠独立。透过打开的窗户,她看到昏黄的日色照进来;看到寂寞的灰尘在暮色中寂寞的舞蹈;看见光滑的织布梭在昏暗的角落独自散发幽寂的光;看见孑立的纺车让她心动又脸红的摇手柄,似乎也在等待那日翩然而至的公子。
有多少个洒满日光的长长午后,二丫就这样伫立窗外,看着织布机,看着纺车,看着整齐归置到墙角的各式农具。一切都和那日一样。甚至日色,甚至鸟鸣,甚至风中绿叶的低唱,青草的絮语,花朵的芬芳。每日清晨,二丫一定把织布房里里外外打扫的干干净净,把当日不用的农具整整齐齐归置到墙角,然后从远处近处门边窗外各个角度去一遍又一遍察看所有一切摆设和他来的那日是否完全一致。有时候她也喜欢采摘新鲜花朵用素净花瓶养在纺车旁。春天的映山红。入夏的栀子。秋日的新菊。雪地的红梅。二丫现在更多爱的是纺纱而不是织布。一个人静静坐在纺车旁,她甜蜜地想到这个凳子是他坐过的。这样一想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和他坐到了一起。但是这木凳是这样窄,无论如何容不下他们两人。那么,她坐到他的腿上去?二丫红着脸,再不敢往下想。她摇起手柄来。又想到这手柄是他曾经握过的。现在她也握起了这同样的手柄来,那么就等同是他握着她的手了?她的双手,虽经长年累月的劳作,因为年轻,仍是这样娇小绵软,仿佛是天边小小的片云,是山中静雅的兰花,是玉匠手中精雕细琢过的美玉。即使握作拳状,亦相同她两弯柳叶眉的微蹙。他看一万遍也不厌。他一定这样赞美起她来。这样的油嘴滑舌。但是她喜欢。二丫一下从摇手柄上缩回手,忽地站起身来。我是不是疯了?魔怔了?二丫一边喃喃自语般自责着,一边朝织布房门外走去。她无心纺纱了。然而甫一转身,又是一眼看到那把半倚在墙角的锄头。她又挪不动步了。那把锄头,他曾细细把玩过的。他手握锄头,在小厮的指导下弯腰锄地的情景历历在目,恍若昨日。她不觉定住了。双手紧握住长长的光滑而冰凉的毛竹锄柄。把自己剧烈起伏的胸口贴上去。把滚烫的脸颊贴上去。把羞涩的红唇贴上去。她再清楚不过的知道,在第八和第十个竹节处,他的双手曾交替着在那里长时间停留。她又是忽地一下扔掉锄头,像扔掉从炉火中拣出的灼红的炭。她为自己的轻薄感到羞耻。她重又坐下纺起纱线来。她一遍遍告诉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雪白的纱线被一根一根接连不断地纺出,就好比她隐秘的情感,被岁月之手在生命的年轮上一遍一遍纺织,一遍一遍蹂躏。她觉出了轮回的苦痛和虚无。这样自甘沉溺的不愿救赎。她苦痛地甘愿。柒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那日母亲病重。二丫背上竹篮到山中为她采药。她寻遍群山。下山的时候见到那座坟墓。其实上山时已经路过那座坟墓了,只是她没有注意。下山的时候,因为远远便看到坟前摆放的十来个圆圆的青青莲蓬,二丫便留意了;她从未见过如此新雅的祭拜死者的方式。不觉走至坟前,清楚看到墓碑上刻着:
爱子秦钟之墓。
又看到生卒年月,细细一算,死者年仅十五。二丫没来由落下泪来。她想象这个早夭少年苍白俊美的脸。想象他的天真单纯和多愁善感。想象他因为剧烈咳嗽一袭白衣上溅落的殷红血滴,慢慢洇氲出红梅桃花的形状来。山风轻拂。墓畔松柏萧萧悲鸣。墓身芳草离离,如想望中他秀美的发。二丫仿佛闻到早夭少年身上散发的诡异迷幻的死亡气息。二丫低下头,又看到足下的青青莲蓬,被祭拜者精心摆出圆月的形状,端放在墓前,悠悠散发出微微带些苦涩的淡淡荷香。二丫伸手从背后竹篮中摘下三朵最大最艳的桔梗花,用一根青草把花枝结成束,也轻轻放在莲蓬旁。一低头又注意到有几个莲蓬上还带些水珠子,不知是雨露亦或泪水,便猜想这祭拜之人或许离去并未多久。她转身便朝山下走去。这以后的路就不觉走得快了。二丫微微气喘着赶到山下时,不见一人。复又抬眼望山。但见遍山草木蓊郁,连那坟墓的所在亦无从辨识了。触目尽是无情草木的世界。二丫当然不知道,自己已迟来一步。他带着小厮,早已离去。不久,二丫母亲过世。实际上她母亲一向身体虚弱,气血两亏。生孩子又多。妊娠年月,便常服柴胡六合汤。有好几次产后昏晕,连销魂散也不得不服了好几剂,虽然贵。至于调养方面,当然说不上,能喝上几回当归羊肉汤就算很不错了。她存年才只四十。母亲过世后,父亲觉得二丫得出嫁了。宁添一斗,不添一口。这时候,父亲好像方才想起这句古话。最小的弟弟也已六七岁了,没有了二丫的照料,勉强也行。二丫出嫁前最后一次来到织布房。最后一次像往日一样端坐到纺车前。橘红夕阳如同忧伤的泪水在窗外静静流淌。二丫不能不想到那个春日午后。不能不想到他。他均匀的呼吸。他微香的鼻息之气。他略略俯下身细细观看她纺纱的样子。他为着她回身轻骂那白净男子。他洁白的孝服从她同样洁白的手臂上轻拂着拖曳而过。这肌肤相亲的刹那,这短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共处时光,这微不足道的一处处细节,值得二丫用一生的时光去回味和怀念,去记得和温暖。二丫对父亲说,我要带上这辆纺车。二丫执拗的眼神和坚决的语气,让父亲欲言又止,终是点头应允。将为人妇的二丫知道,有些人生的梦从此便不能再做了。二丫不觉得悲伤,只是寂寞。似又痛入骨髓。直面现实是这样惨烈,就像在月圆之夜直面裸露着的鲜血淋漓的伤口。要用一生的时光和泪水来愈合。亦有可能,一生都愈合不了,余生都要带着这巨大怆伤独自走向归途。捌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二丫的丈夫实在没得什么可以说。你走在集市或者乡村小道上,随手指一个三十上下相貌平常一脸憨厚的男子说,这就是二丫的丈夫。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或者表示怀疑。婚后的二丫便开始了漫长的生育生涯。当二丫生下第五个女儿的时候,她再不想生了。同时她也早已失却了翁姑之爱。他们对家中诸凡事务的处理原则是,能指得上二丫的,绝对不用别人。成日二丫这个二丫那个的不离口。恨不得把她掰成八瓣来使唤。扫地、洗衣、做饭、烧水、纺纱、织布。种瓜果蔬菜、收五谷杂粮。二丫终日的行色匆匆。她脸上既没有欢喜亦没有悲伤的痕迹。二丫觉得自己活着,就像是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从春到夏,忙着发芽、生长、开花、结实。若来了风雨,它们就被雨打风摧;若来了霜雪,它们便枯萎死亡。若是风和日丽,它们便生长,亦看不出分明的乐与愁。二丫觉得自己活着,就像它们,心头无喜亦无嗔。她觉得自己的心,安宁的就好像月光下的一片沙滩、一池太湖石,任潮起潮落、雾锁云开,她只是独立无语。是从何时开始,二丫习惯了每年春天都要种上一畦茄子。等到初夏茄子花开,悄悄摘下它们的紫色花瓣,放入口中,嚼碎咽下,以此来避孕。渐渐的,二丫喜欢上茄子花的娇小、绵软和微香。每年桃杏花开的时候,二丫总要挑上一个阳光和煦的春日,拣拾它们飘落一地的花瓣,晒干、研碎,尔后和入胭脂水粉里,以此来润泽肌肤。因此二丫虽然终日劳作,仍然是那样年轻和美丽。每日清晨她去河边汲水洗衣时,有时因为太累,便在光滑平整的洗衣石上歇息片刻,这时候,过往行人,没有一个不惊叹二丫的美貌。二丫却将两眼长久凝望脉脉流水和水底流云岸石的静默倒影。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不止一次,二丫一遍遍问自己,葆有这美丽容颜,到底有何意义?玖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二丫一直保留着夜晚书写的习惯。但是自从嫁入秦家,这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了。极偶尔的,在丈夫孩子入睡后,二丫独坐灯下,默默填词赋诗,不觉泪下。
有几次被婆婆发现了,便心中不悦,抱怨道,大晚上的,怎么老点着灯?是我在抄金刚经。二丫淡淡答道。没成想婆婆倒笑逐颜开了。写经是好事啊,写经好写经好。几时你抄好了我送到庙上去,但愿菩萨保佑我早日抱上个大孙子。这世上的事有时还真无巧不成书。这年秋天,二丫竟又怀孕。次年便顺利产下一子。一家人喜得合不拢嘴。二丫却表情木然,无喜无嗔。生下儿子后的二丫便很少外出劳作了。更多是在家中纺纱织布。又是教女儿们唐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二丫一句一句的教,女儿们一句一句的跟。又是满耳读书声。从前的日子仿佛又回来了。只是岁月流转,物是人非,空余伤悲。佳人虽犹未老,却早已为人妇、为人母,早已绿叶成荫子满枝。思量至此,二丫不禁涕泪涟涟。这人生,为什么要有这大好青春,要有这实现不了的美丽的梦呢?有梦,老天爷却不给机会、不给希望、不给未来。只是苦。只有苦。一直苦。守一辆车,等一个人。哪怕倾尽一生时光,亦只是等来无望。这漫长到比漫漫一生还长的无望啊,二丫觉得自己再也等不下去了。这年的下半年,二丫开始断断续续服用丹栀逍遥散。她不去买现成的加味逍遥丸。常常是带上女儿们,到深山里去拔柴胡、寻桔梗、挖野牡丹。二丫渐渐喜欢上中药的苦香。二丫全身心沉浸到采草药的欢乐和中药材木质化的芳香里。蓝天白云。群山如浪。芳草无垠。二丫的心常常因此飞到辽远的天边。二丫有时甚至喜欢自己生着这忧郁的病。她日复一日恋上了这忧郁的病和中药的香。她不可救药。她一早便知。这么多年过去了,二丫的纺车一直没有坏。铁质的手柄,因为无数次的被使用,变得光滑无比。在幽暗的角落依旧独自散发柔和幽寂的光。木制的转轮,遥远而亲切地永久重复着那个春日午后羞涩而甜蜜的歌。忧伤如洁白的线,被一根一根源源不断地纺出。二丫厌倦了这样的轮回。但是一次次在纺车前坐下,仍然是心头一阵暖,眼前一阵热。二丫想知道,这古旧的纺车,如果没有人去蓄意破坏它,它是否要千年万年的存在下去,纺老一辈又一辈的人?昔日的佳人老了,昔日的梦还在。但是梦里的人走了,却再也不回来了。用一生的时光去痴痴等待,依旧等不来。梦却还在。梦永远不会老,不会死,要被流转着一代一代做下去。只是,这无望的梦,还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吗?拾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那日,二丫又和女儿们一起去深山采药。后来她们在山中走散了。二丫独自一人在深山里闯。然后她看到那座古庙。古庙陈旧而破败。连名字都没有。山门旁却贴着一副对联,倒有些新,和古庙的破败明显不相称。字也写得好。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二丫对着这对联端详了很久。但觉这字迹非常之熟悉,熟到起腻的程度;却反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何人所书。待二丫终于寻到女儿们和他们一道下山时,一路只管低头沉思,连女儿们的说笑打闹亦置若罔闻。二丫永远不会知道的是,他化缘回到古寺时,她早已回到家中。这是他们的第三次错过,亦或许是轮回生命里的不知多少次。这天晚上,在梦里,二丫终于忆起,这古庙对联就是梦中他的笔迹。梦醒后的二丫却只管细细琢磨起“假作真”、“无为有”这六个字来,悟道参禅般翻来覆去的念,心中忽有所悟,又止不住泪落如霰。二丫一遍一遍问自己,为什么要用一生的时光去等待一场假作真、无为有的虚幻的梦的实现呢?那个春日午后翩然而至的白衣少年,原来不过是杜丽娘在自家后花园午后打的一个盹。然而幸运的杜丽娘等来了她的柳梦梅,二丫却用尽一生的时光也等不来她的那个他。第二日起,二丫便再不到深山采药,更不用说寻访无名古庙。二丫没有了这样的兴致和痴情。亦不再熬药。她现在只吃现成的加味逍遥丸。渐渐的,药亦不再吃。没过几日,二丫便决定将旧纺车卖掉,换辆新的。婆婆自然又是阻拦。二丫道,这纺车太旧了,买一辆新的,好使,纺出来的纱线自然又多又好。还省力气。只有二丫自己知道,真实的原因当然不是这个。新纺车很快便被选中并买回。二丫终日在纺车上忙活,然而纺出来的纱线并不比从前的多和好。婆婆双手一摊道,看,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丈夫在一旁悄声道,娘,您老得体谅她身体一向不好,这一程子又在病中。婆婆道,既这样,何苦非要作践钱买辆新的?谁还指望她纺多少线来着?二丫对他们的角口忽然觉得厌倦。她厌倦了这人世的一切,更厌倦了这一世都要这般庸碌卑暗千年如一日不被读懂的活着。她又何曾有过一天活出一个真实明亮的自己?不久二丫病重。终日缠绵病榻的时候,二丫开始常常梦到舅舅和母亲。在梦里,二丫见到舅舅年轻的笑脸。见到母亲面色红润绿鬓如云,再看不到一丝一毫生前的虚弱苍白。而她,亦不再是生育过太多子女常年患着忧郁病的女子。她还是他们眼中那个扎着漆黑水长辫子的小小女孩。能言善辩。才思敏捷。锦心绣口。梦里的天地永远是美好的往昔。一丝未经沧桑岁月无情风雨的驳蚀,更不用说世俗泥淖的浸染,脱离真相般永远那么洁净无着。它仿佛是一片飞不到人间的云。一滴落不到尘世的雨。一朵盛开在天宫四时不谢的花。频繁的逝者入梦,让二丫渐渐迷恋上死亡摄人心魄的美和它对人心灵如清水莲花般的濯洗与净化。从此二丫静卧病床的时候,再不愿把头转向临窗的那一侧,一任窗外日落月生、新菊初绽、桂子飘香。她自有梦里的美好天地,不与尘世相关。拾壹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那日,二丫忽然把丈夫叫到床边嘱咐道,你们都叫我二丫,其实我有名字的,我叫楚月寒。我希望自己死后,能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自己本来的姓与名,而不是秦楚氏。
话只听到一半,丈夫早已哭得泣不成声。二丫便有些烦了,道,人活百岁,谁还不是个死?这生关死劫,谁又能躲来着?丈夫勉强劝道,人吃五谷杂粮,谁还能不生灾害病?你只把心放宽着,别整日胡思乱想的。再多吃上几副药,一准就好。才四十岁的人,哪里至于?不久,二丫便开始说胡话了。她嘱咐女儿们道,你们的大姐快出嫁了吧?让你爹留意着,找个忠厚本分人家,过安稳日子最好。而实际上,她的大女儿明珠前年就嫁人了。都有孩子了。又道,春天来了吧?桃树杏树都开花了吧?你们替我选一个晴好的天儿拣些落花晒干研碎,我好带上。而那时,正是深秋十月。又对被一家人视若珍宝才四五岁的儿子说,等再过两年,让你爹送你到私塾里读书去。小时候我在你舅爷私塾后面的绡山书屋里读书。那地方风景真好啊。书屋对面就是高大的四屏山,把绡山书屋像绿色摇篮般围了个遍。山中四季翠竹青青,野花遍地。每年春天来的时候,山中便有一种鸟,叫声比黄鹂还好听,它的羽毛像缎子一样光彩照人,每次它打我们绡山书屋的蓝天飞过时,谁都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可是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也没有人去赞美它美妙婉转的歌喉。而事实是,舅舅的书屋没有名字,对面的山岗亦不过是寻常土丘,同样没有名字,更不要说美丽风景和婉转鸟鸣。鸟鸣或许有的,不过是斑鸠猫头鹰之类。婆婆断定二丫是活不长了。这样的胡言乱语就是人之将死的最好预兆。她接着便举了好几个她亲见亲闻的家里过世亲戚的例子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又忙着嘱咐儿子通知二丫娘家兄弟以及暗中预备二丫的后事。过世前三日,二丫已不能再说出一句话。她最后只能艰难举起右手指向自己的陪嫁书箱,嘴唇动了半日,却再说不出一句。一家人便猜测,一定是要这书箱陪葬,毕竟她读了一辈子的书,一有空便把里面的书一本一本拿出来细细的读。而实际上二丫的真实意思是,把箱内的书全部烧掉。佳人一生诗书误。若没有这磊磊一箱书,若不会断文识字,做一个寻常村妇老妪,她这一生亦未尝不可以过得幸福,即使是盲和无知,亦是圆满。更何况,她还有一个虽然不懂她却还算疼她爱她的丈夫。只是到如今,说什么都太迟了。这正面细细雕刻着数丛纤纤幽兰的小小书箱,原来这里面装了这一世太多的的爱恨悔悟。不说也罢。
拾贰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二丫过世以后,她丈夫将书箱里的书整整齐齐摆放到棺材里。
婆婆在一旁忍不住小声嘟哝道,真没见过这样的怪人。最后从书箱底部翻出厚厚一沓写满字的纸来。众亲戚们围拥上来,争着一看究竟。那片夹在纸稿里的写满心经的干枯桂叶就这样被翻落地下,当然无人留意,很快便被众人杂乱的双足踏得污碎不堪,再难辨识。婆婆也忍不住踮起脚凑上去道,写的什么?二丫丈夫抽出一张很艰难的一字一句念道,暖雨无情漏几丝,牧童斜插嫩花枝。小田新麦上场时。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吹黍又嗔迟。日长酸透软腰肢。
念完后大家不知所云。忍不住又抽出一张艰难念道,春不见,寻过野桥西。染绿淡红欺粉蝶,锁愁浓绿骗黄鹂。幽恨莫重提。 人不见,相见是还非。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清泪又沾衣。山远夕阳低。
念完后大家面面相觑。忽然二丫丈夫一拍后脑勺道,我想起来了,这是二丫抄的——抄的——宋词。婆婆不耐烦的摆手道,放进去放进去都放进去,我当什么呢。她本来还想再说几句难听的话,碍于二丫兄弟媳妇们都在场,也就罢了。二丫过世后不久,那年大寒时节,为了却她的生前遗愿,丈夫到底为她立了碑。但是在刻碑文时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楚月寒三个字来。只好又跑去问二丫的娘家兄弟,他们也是绞尽脑汁的想不起,甚至都没听过,不过是从小到大都一直长姐长姐的叫着。他们甚至怀疑二丫是否有过这样一个名字。其时二丫父母已世过世多年,当然更无从问起。末了不得不循着旧例一般也刻上秦楚氏之墓的字样。在一片乱坟群中,和其它坟墓并无不同。
拾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叁
三年后丈夫再婚。这回娶的女子,非常之贤惠,照二丫婆婆的话说。只吃亏了一样,是个寡妇;人又生得黄胖而矮,好在没有孩子。二丫婆婆逢人便翻旧账道,我要不是念着和二丫的姑侄女情常,才不和她家结这门亲呢。真没见过二丫这么个怪人。倒可惜了她那花容月貌。
这女子婚后不久,有一次打扫卧室房间,无意中从床角处发现一张写满字的纸来。字体端正娟秀。她也识字不多,很艰难的一字一句念道,我丢下纺车,一径去了。心下惘然。他走时,我怀里抱着小兄弟,同着几个东邻女伴,远远看定他们的马车。我看他上了车,出来走不多远,便恨不得上了车,跟了他去。料是无人依允的。只得以目相送。争奈车疾马快,一时展眼无踪。
念完后觉得莫名其妙,字虽然都认得,但是不知道说的什么。又拿给他新婚的丈夫看。丈夫却看也不看随手把纸一团,一舒手便扔到窗外的沟渠里,回头对他新婚的妻子笑道,不过是孩子们从前读书识字时胡乱写的字罢了。原创简介
作者 :午梦堂主,古风沐沐粉丝。
排版 | 灼华
图片 | 网络
头条与专栏征稿
1、文体题材:古风相关,古风爱情故事、正史野史八卦优先,关键是内容吸引人,字数1500以上。
2、投稿格式:标题+作者简介+正文,每段空一行,开头不用空两格,推荐在石墨文档编辑好后发送分享链接。3、投稿方式:第一次投稿发送至邮箱1529349025@qq.com,过稿后分配小编对接,之后可直接发文章链接给小编或作者群。4、过稿奖励:目前稿费5元一篇,阅读量过500奖励5元,赞赏一半给予作者,随着公众号的发展会进一步提升稿费。5、审稿回复:可过稿但有些瑕疵的文章,小编会给予修改建议,未过稿也必定会告知原因,邮箱投稿如一周后未回复,可加主编微信询问进度。6、注意:所投稿件要原创首发,不得抄袭,不得洗稿,不得一稿多投。过稿稿件,支付完稿酬,沐沐拥有所有权,可任意处置。点在看、评论的事情就拜托啦~
上一篇:【“书香司法·悦读明心” 征文大赛佳作选登】感受唐诗的魅力——读《唐诗简史》有感
下一篇:栾川“我看第三届高速免费”主题征文活动,今日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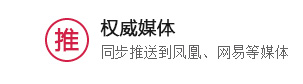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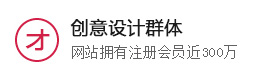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