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新居几天后,正值中秋。清风不等明月,鲜活的面容似乎还在飞扬,熟悉的背影已转身,人生的悲怆,在于故事才开始,却缺少主角。我主持祭月仪式,希望亘古不变的月光,告慰我祖辈和父辈对新居70多年的期待。就一个国家民族来说,70多年的时间不长,记录着开国元勋们的口音腔调、手势步履的视频,常常勾得我澎湃满怀,那些都不是暗淡的刀光剑影、远去的鼓角争鸣。70多年的时间很长,安居之梦,熬走了两代人。期望沉淀下来,成为沉甸甸的嘱托,再怎么超脱也不轻盈。爷爷是在旧社会当过警职,过去的“风光”,必然使他成为家乡政治运动的“展品”,一次也没有逃过。他既无田地,也无房舍,甚至也无劳力,三个儿女嗷嗷待哺,体弱身单的妻子给人家做点针线活维持生计。基于特殊而照顾,也基于乡里人的善良,同意我爷爷用村东过街楼的小块地,换取漏阁三小间瓦房。百年老屋,成为爷爷一家的安生之所,一住就是60多年。为此,我的姑妈,曾特意地去感激年迈的老支书。我的88岁的伯母,也曾哭泣着向我描述着我爷爷奶奶的辛酸。她说,我的爷爷,没有自己的被褥床铺,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居然是和邻家的族兄蹭床过夜!我父母都出生于1947年,一生挣扎在温饱线上,虽然有心,却无力起居建房。80年代收购两间厢房,作为猪圈,铺陈开农家人正常的生计。在堂伯父的协助下,供我大学毕业。我和弟弟,中学都睡在楼道上。木条扎成的围栏,篱笆糊上报纸来挡风。奶奶生前的居所,后来成为我兄弟的婚房。我的婚房,仅放得下一张双人床,局促得,让我回老家一回,惆怅一回。我的母亲身前,不止一次地诅咒过人挤畜拥的居所,她离开的时候,我36岁。死尽其哀,丧尽其礼,局促的居所,第一次让我感受而立不立也不孝的屈辱。我为此自责良久,哀伤良久,酝酿良久,再怎么苦,也要盖房起居。我的母亲来不及看到我们起楼盖房,离开了我们;我的父亲,恰好在房子封顶前一天,离开了我们。许久不曾走动的他,居然有一天走到房子前的树墩下张望。为此,我们商量,停灵两天,等房子封顶再出殡,也算是替他完成心愿,希望他入土之前,把子孙安家的讯息,带给我的苦命的母亲,带给我的爷爷奶奶。中秋过后的黄昏,晚风微凉。我特意回老屋探视,两代出生地,两代人成家的安置所,两代人的希望和屈辱,正如秋雨丝线一般的淅沥。百年的老屋,落寂凄凉,破旧的斗拱,渗漏雨滴,楼梯斑驳,木门咯吱,纸糊的墙,似乎映衬出童年斑斓和少年的青涩,风华正茂的青春,都留在时光里。窗外山抹微云,水染浅绿,院内,芳草萋萋。我站立在漏阁,心中久久难以平息。与老屋相关的记忆,一刹那间升华,如断了线的珍珠散落一地。漏阁天井的墙面,伯父震公书写的“万象从新”的大字,在湿漉漉的空气里展现着它抗争的顽强。站立在他的字迹下,我第一次感觉,字里的精神气质,直逼我的心灵。多年来,这种悲凉,成为我们兄弟发奋的动力、团结的根源。伯父震公已经离世多年,和我母亲一前一后。思念道不尽我此刻的凄凉,我静静地呆望着老屋,泪眼弥蒙。再也唤不回那些亲情,那些满满的爱,那些叮咛嘱托,那些温馨牵挂……万象必须从新,伯父题字的期待成了现实,老屋却再也承载不起如潮的笑语,再也负荷不动风月的情韵。记忆刻骨铭心,回忆也能下酒,我在新居田园风情的窗景,与老屋同醉,与岁月沉吟。
长按二维码关注“大理时讯”ID:dalishixun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大理时讯投稿邮箱:dlsxtg@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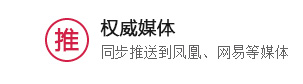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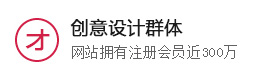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